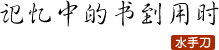![]()
|
|
||
|
网上看过多篇我的多少本书的作文,好几次差点参与意识发作,准备冲过去发言。你奶奶的,就你读过书啊?搜肠刮肚一会,觉得奇怪:为什么人家被那么多书影响得一塌糊涂,我却没有?好没文化啊。还是没记性? 今天是个阴天,沉闷,压抑,皮肤紧张,思维活跃,开始回忆。 记得小时候,恨读书。 3岁开始背三字经,家长期望我方七岁,举神童吧。一年之后,三字经背得烂熟,其间多次被一条寸半宽,一尺长的裁衣尺打肿手板,还不准哭。家长说:男子汉大丈夫,打脱牙齿往肚里吞。奶奶的,三岁就要求挺直腰板做男子汉了。打人的是奶奶,长脸,不笑,皱纹很多。 七岁那年,奶奶死了。我没哭,也不说话,披麻带孝站在棺材前面。 奶奶静静躺着,姑姑们不停哭泣,亲戚站满长街。后来,锣鼓喧天,号角齐鸣,奏的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八姑过来搂着我说,哭啊,奶奶多疼你,你要孝顺啊。 我硬梆梆底站着,象棵树。树是不会流泪的。也许就是那天,把三字经都忘记了。焚尸炉的火在铁活门后面烧,你说,能用三字经表达心情嘛? 那以后,会疼,会伤心,不会流泪,代之大笑。 大学寄宿不讲卫生,冬天干燥皮肤搔痒,用肮脏的指甲去抓,感染了。学术上叫毛囊炎。 医生用镊子一根根拔腿上的毛,碘酒消毒。疼。 我开始笑。大笑。狂笑。笑着笑着医生咣几扔下镊子说,我操,有病啊。跟着狂笑。我说,是啊,你不正给我治嘛。医生说,笑什么?死人啊。他笑着说话,几乎被口水噎死。你看,差点谋杀一个医生。我就说,不笑了,给你背三字经。就背。原来都记得。医生又拿起镊子和粘满酒精的棉球。他说,这比傻笑好点。 唯一一次反复三次全文背诵三字经。没人在旁边监督是否背对了。我想,应该一字不差。医生和我都没再笑。后来,好了,又忘记了三字经。 小学时,操场被民兵指挥部占用,搭库房放机关枪迫击炮。没法上体育课,老师就给我们讲故事,宋江和李逵什么的。开场白这么说:水浒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大意如此。当时有个说法叫做口诛笔伐。揭画皮。 老师揭开一本绿皮的水浒,我们进入一个豪迈的世界。一个学期过去,宋江他们还没投降,老师调走了。换一个老师居然要我们抓着椅子背压腿,下腰,倒立,走廊上练空翻。后来有个同学得了体操方面的全国冠军,这是后话。我尽记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故事,练得不专心,所以没成体操冠军。算是转型不成功。 水浒这套书,我们家有。在猪肉凭票供应的年代,我开始读这本古老的书。看到哪位英雄吆喝切5斤熟牛肉,打两角酒来。我就吧叽一下嘴,把书页撕下一个小角放舌头上。二姑见到说,这小孩肚里有蛔虫。多年之后,形成一些偏见,譬如:水浒英雄多是回民,因为他们很少吃猪肉。又或者蛔虫是吃纸的,它们生活在我体内。 水浒是翻着字典读完的,之后基本具备高小语文水平了。读完水浒的晚上,奶奶去世了。 那天晚上,我坐一个小板凳,书放在奶奶膝盖上。奶奶用手摩着我头顶的硬发,和几位姑奶奶说话。她们都坐着红漆的太师椅,喝放了红姜和黄豆的绿茶。 讨完方腊,水浒英雄七零八落,我很快地追寻他们的终结。合上书时,奶奶按着我的头顶说,我这一生讲起来真是青红紫绿。我眼前就闪了一点点五色缤纷。 我去睡觉。 奶奶进屋关掉25瓦的灯,拉亮了那盏3瓦的灯。那点亮光不过2寸。奶奶说,头晕。我也躺会。 我的床是那种有踏板的,象个屋子的木床。床板上刻着许多小人,包含了一些故事。我从未有仔细读过,家长也不给讲。成年后想来是儿童不宜吧。 深夜被吵醒了。家人围着床。奶奶在我身边,硬了。 床踏板被隔壁秦叔叔踩断了。爷爷踢翻了马桶。空空的马桶空隆隆响。在夜晚,我紧张,颤抖着把眼紧闭。那是恐惧吧。我听到人们在黑暗中叫喊。 我又把水浒忘记了。包括最刺激的智取生辰纲。 20年之后,和几个朋友打麻将。屋子里烟雾缭绕,只一盏吸顶灯挂在麻将们的上方。一付清一色三飞叫,雪茄被我咬断。手机响。朋友望着我。 一哥们在云南被绑架了。他对公司很重要。我们立即出发。 穿过苗岭,车轮不断地尖叫,云雾在窗外。我们在群山中上上下下跑了3天,途中吃过三次饭,轮流开车和睡觉,不喝酒。快到攀枝花,一哥们下车撒尿,用冲锋枪向一只迷途的野兔打了一个点射。枪声暴躁。我一直惦记着那付清一色。庄上自摸就是6千。想起来都要笑啊。 第四个夜晚,进入昆明。深夜冲进一居民楼。后来一致庆祝,那房子是个木门。我和小鸿一起撞过去,整个门倒下。我压在门上,小鸿压着我。紧闭眼,人们从背上跨过去,踩着我的手指,手指不疼。人们在黑暗中低沉底怒喝。光线掀开我的眼皮,小鸿把我拉起来。 事情就这么结束。 事毕,不记得在邦克还是金龙,一群人喝酒。昆明是个好地方,四季如春,姑娘如花,五湖四海的都有。倚红偎翠把盏言欢,竟哼哼赤日炎炎似火烧…… 说到姑娘,想起一本书,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是一本合集。第一篇是沈从文的边城。还有一个塔里的女人。沈从文后来读过好些,感觉挺优美,现在去猛洞河之类的地方还能找到那种不爱搭理世界有些清苦的优美。可以为不如艾芜用挂在胸前的墨水写出来的那种漂泊。不提了。 无名氏的小说最适合14岁左右,下巴略有些青苗,心中陷入绝恋的男孩子看。原文不记得了,都是那种一串串动词,被动式的句子,吃我吧,喝我吧,咬我吧,舔我吧,撕我吧,碎我吧……大约就是这种调子。 14岁看中一个mm,没什么道理,服从荷尔蒙的召唤吧。在蓝色晒图纸上面使用粉红色墨水写了一封吓人的情书。包括14行,大约是仿勃狼您夫人,抒情诗,主要是雪莱拜伦和叶芝的词汇和调调(翻译的啊,不是原文)。还有词,鹧鸪天,满江红之类,字数对得上,韵角肯定不成曲调。剩下的全是无名氏的套路,包括上面那段。 浅蓝的纸上字迹显得有些发霉,就剪了一个火红的家伙贴在一角。日后不清楚是一颗心,还是一个苹果,还是两瓣屁股。可疑。 一张2号纸折了四下,发作业的时候夹在本子里交到mm手上,意味深长和她对了一眼。上课望着那飘飘长发痴痴发呆。 日后牵她的手,问她。她说,好怕怕,真想还给你。我问,怕什么?她说,好像请求我将你凌迟还不准用工具。这是对我无名氏式情书的评语。 老师知道了,骂我。不好好学习,将来烤不上大学。只有去拖板车,挑大粪。狠朴素的道理。 我倒无所谓,把mm吓坏了,跑了。Mm总是爱干净的,怎么肯去干那个。老师给我一个“思想复杂”的评语,成为档案中一个暗号。 Mm就此不再理我。什么狗屁诗歌浪漫也不记得了。常常下午到同学家听唱片,蓝色绿色的小唱片,黑色硬塑料的大唱片。陈方圆唱英文歌:where do I began to tell the story of how great love can be……我是那个预科生,又穷又聪明。……I know I need her till the star borm away…… 胡说。 14年后,和mm一起打麻将,脚们在台底纠缠不休。午夜,她打开手机,娇滴滴地说,老公,今天输惨了,要扳本。你一个人在家要乖啊。 那个时候啊,手在裤兜里,摩娑着酒店的钥匙牌,手心手背都潮乎乎的。我想,该被千刀万剐了,14年前注定的宿命将得偿所愿。Yesterday once more。……?? 这种关头还需要记得作家或者诗人说过些什么吗?I am a man。 关于男人,有本书是伟大的。D.h.劳伦斯伟大的著作,查泰来夫人的情人。80年代中期,有准确消息说,此书首印四万,定价10元,征订单发到了大学各个宿舍。不久,继续有不太准确的消息,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潘达雷昂上尉的劳军女郎,玫瑰梦,丑陋的中国人,叫四大禁书。印出来也要烧掉。 购买和阅读这四本书立即成为时尚。 狠荣幸地说,我也时髦过。 玫瑰梦不算好,比目前一个什么男的小说差不多。潘上尉的劳军女郎不如另外一本城市与狗好看。丑陋的中国人只记得一个酱缸蛆的词儿了。但我想说,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实在是,实在是了不得的一本书。就个人体验而言。 一本解决个人幸福的书,实在怎么形容也不过分。 中学上生理卫生课,老师是个老头,外号最可爱的人。昔日的志愿军,战俘。说话怪异。那天,他走进课堂说,今天,看电影,讲一些大人的事。男女同学分开看,课后不准交流。男同学排队去第一放映室,看有的。女同学排队去第二放映室,看没有的。 我们不得不哄堂大笑。 这课的内容关乎生理机制,和幸福无关。全长30分钟。 苦读查泰来夫人的情人,历三个夜,耗9只烛。 其间,上铺熄灯就钻进蚊帐弹吉他,阿拉罕不拉宫的回忆,无休无止的轮指让人沉溺。上铺后来成为一个大腹便便的贪官污吏。隔壁下铺练气功。当时气温低于10度,这厮着一条遮不住银毛的三角裤,站一桩,头顶一线白气冉冉升起。我忽冷忽热,酒色财气四大皆空,神游物外。到最后,竟觉天地玄黄,远古洪荒,男人和女人散发为旗赤身而歌,远处猛兽咆哮此起彼伏。 不知个人野兽了,还是纯真了。心底旋转着一小点暖暖的气,烛光闪动中,爱人的脸缥缥缈缈,美艳万方。 第四次阅读此书和爱人一起。同时搭配四本龙虎豹,计生用品若干,苦味雪茄一包。 爱人说过的一句话日后总是记得。她说,我飞起来了,上了喜马拉雅山。 靠,想起这话,一身的毛孔就张开了。 劳伦斯这本书毕业前送给了学弟,送人幸福,手有余香啊。成为真正的男人和女人就是幸福,这不应该是说来让人脸红的道理,过程则须各人自行推理。 还读过很多书,看过就忘,没什么用,所以不再记得。 经过许多事,忘记书,记得名。忘记故事,记得滋味。最后,你会忘记容颜,忘记过程,忘记以为将永远刻骨铭心的所有事。回忆支离破碎如千疮百孔的旗在风中飘啊飘,不象征什么,不代表什么。 有个电影里说,人分两种,一种天文学家类型,另一种则是要做宇航员。第一种人能远远观察研究美丽玄妙的事物但不会危害自身,而后一种去探索投身未知的世界大约会要惊心动魄甚至以命相许。 我曾经想,大约是,后一种吧。忘记书,折腾一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