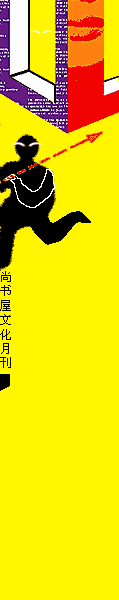
|
末班爱情之火车上 卢小狼
|
|
我又一次坐在最廉价的火车上,那种火车每一站都停,车厢闷热、拥挤,连过道里都站满了人,我满脸堆笑的询问了几个有可能提前下车的人,然后在其中一个身边站住左右张望。随后我拿出一支烟和一本米兰.昆德拉的《生活在别处》,其实我并不十分喜欢这本书,我带这本书出门的目的就是要表明束缚已经被撕破,是对过去那种郁郁寡欢生活的遗忘。 列车的两旁是破落的农庄或寸草不生的荒地,偶尔也有河流,天空是明亮的,这一切视觉感受或许都是今生只有一次的,再次看到它已经改变,就象在梦中。当经过田地时,会看到劳动的人们和拖拉机手,还有田边的机井,垄上奔跑的孩子,我觉得这些是熟悉的,于是我合上书,再次点燃一根香烟,充分享受自由的时刻。 我面前坐了四个人,一对恋人,一个老头还有一个瘦的青年,他们都不说话,恋人相互依偎,老头子发呆,青年人抽烟,那个青年脸色蜡黄,干瘪,仿佛电影里的灾民,我饶有兴趣的打量着他皱巴巴的西装和条绒面的布鞋,想象着自己如果不是早早离开农村,一定也是这种样子。终于那个老头子下车了,我坐在那个青年人里面,我占了大部分地方,那个青年只好换个姿势,把脚放在过道上。大家都不说话,我又拿出《生活在别处》,准备消磨掉漫长的旅程。 那一对男女终于说话了,他们仿佛一开始是木头人,而现在是两只唧唧喳喳的麻雀,那个女人语调极为夸张,忸怩作态,他们在讨论一些无聊的话题,是的,从他们遮遮掩掩的暧昧表情我可以确定这一点,我竭力把注意里从他们身上挪开,进入到书的情节中去,但却做不到,我深深后悔自己没有带一本侦探小说,那样可能会更吸引我一些。他们谈话的频率开始变快,声音也开始放肆起来,最后他们甚至在我面前开始打情骂俏,我只得把头低下试图睡一会儿。可是那个女人在我头顶上打了个喷嚏,我感觉她的鼻涕喷到了我的耳朵上,我生气的抬起头,狠狠的盯了他们一眼,随后我又低下头,因为我刚刚从工作的压力中解脱出来,在火车上争吵实在很不值得。 她一定感冒了,因为她又在我的头顶打了个喷嚏,比刚才那个还要彻底,我听到他们俩个的笑声,我对自己说,这太过分了,我要教训这两个混蛋,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否则他们一定会把我当成傻瓜的,我抬起头,对他们说,不要再对着我的脑袋打喷嚏,我不希望在车上和人冲突,但那个男人立刻大声问我,是否想找碴,我说他妈的是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他把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扔向我,而我则把《生活在别处》当做武器抽了他的脸,他咆哮的和我扭打起来。 我是个本份的公务员,平时只是做一些琐碎的小事,身单力薄,所以我很快在打斗中占了下锋,幸亏车上的其他乘客把我们拉开,我才不至于吃亏,当我坐下来气喘如牛的时候,他继续挑衅的盯着我,我心虚的垂下眼睛。我旁边的那个青年人开始注意我,并且他更换了坐姿,使自己更舒服一些,显然刚才发生的一切极大的鼓舞了他,他笑眯眯的问我,是否可以给他根烟抽,我抽出一根递给他。我继续看我的书,因为我绝对是不可能睡觉了,正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那个小个子竟然不说一声就拿起我放在座位上的水喝了起来,我又一次恼羞成怒,但我压抑住了,因为我实在是不想再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更令人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坐在我对面的那个男人居然脱下鞋子,把脚放在我的座位上,如果没有发生刚才的事情,或许这不算什么,但现在我无法忍受这种轻视,我偷偷从包里摸出一把小刀,象电影里那样,看也不看,果断的向我旁边刺下去,只听到一声惨叫,竟是我旁边的人发出的,不知什么时候,对面的人把脚抽了回去,而我的同座的手却放在那里,他手上的伤口血流如注。他捂住伤口大声嚎叫,很快他的同伴都聚了过来,他们都象是打工者,我不停的道歉,说好话,并拿出钱来,但没有人为之所动,每个人都面无表情,他们把我从座位上拉到过道上,天,鬼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我在一种强刺激下醒来,我对面站着一个暴怒的乘务员,他一定用什么在我的脑袋上打了一下,因为我感到头疼欲裂,我那本倒霉的《生活在别处》已不在我的手中,它掉进了乘务员餐车里的汤桶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刚才打盹的过程中。 我沮丧的坐在两节车厢的中间,手里拿了一份盒饭,在我的身边还摞了九份,是那个乘务员逼迫我买的,我的《生活在别处》也被他从窗户里扔掉了。列车依然缓慢的行进,在每站都停,有很多人上上下下,大家都很忙,而我,只能蹲在这里,吃这些难以下咽的盒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