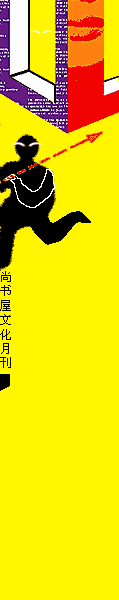
|
看川戏 玫瑰水手
|
|
现在说起小时候看川戏的情形,印象已是十分的模糊了。 只记得台上几只明亮的汽灯“呲呲”地响着(那时松溉还没有通 电),一个年纪不算年轻的女人扮的小姐甩着水红长袖,咿咿呀呀幽 幽怨怨地唱,唱着唱着,台后帮腔的齐声和上一句,把我从瞌睡中惊 醒那么一下。川戏里,才子佳人的情节很多,青衣花旦们长声悠悠地 互表衷情,一个字总在嗓子里回旋半天,把我的瞌睡一点一点地勾出 来。 看川戏对我来说,是一件极苦的差使。但奶奶因为眼睛不太好使, 看完戏回家需我来充当拄路棍。所以几乎松溉的每一场川戏我都没能 落下。 记得那时候总共看过三部川戏没打瞌睡吧。一部是《十五贯》, 里面的唱腔少,对白多。娄阿鼠鼻子上点一个白点,走路只前脚掌点 地,双手跟猴爪子一样吊在胸前,眼珠滴溜溜转,配合后台敲的小鼓, 活脱脱是只老鼠!本来是个杀人越祸的故事(当然还是少不了才子佳 人的佐料),却因了这娄阿鼠让我整晚爆笑不已。第二部是《水漫金 山》,这是《白蛇传》中截选的一段折子戏。《白蛇传》整部戏很长, 大概要演三个多小时,戏中许仙和白娘子从头到尾咿咿呀呀,甚无趣 味,到水漫金山一节时,大多弄一大帮人,把锣鼓敲得山响,走几下 台就了事。这次,却是外地的一个班子(松溉没有自己的剧团,演戏 的都是外地来的班子),专门演水漫金山这节。果然气势不凡,虾兵 蟹将的装备很专业,不象其他戏班,只在头上戴个虾头象征一下了事: 龟军师真的背着厚厚的龟壳,头一伸一缩的;虾兵都会翻跟斗,一连 翻十几个;蚌精是些很漂亮的女子,蚌壳一开一合,突然夹住了法海 的屁股……场面热闹得很。第三部也是《水漫金山》,却是我那时唯 一看过的一部木偶戏。木偶做得很逼真,以至于白娘子变身为一条巨 蟒的时候,我被吓了一大跳(我最怕蛇)。木偶的动作很滑稽,弯腰, 身子一折一折地折下去(这个动作我后来学了很久才学得有那么一点 象样,结果把所有人都逗乐了)。木偶也还是要唱,但看不见嘴动。 据说做得高级的木偶嘴会动,眼会转,但我却一直没有见过。 比较而言,我还是喜欢听说书。一来,不会打瞌睡(说书人有惊 堂木,时不时猛拍一下),二来那里有胡豆吃。说书一般在镇上最大 的茶馆,如果某天茶馆外贴出海报,说邀请到某某著名说书人,说全 本《七侠五义》,那么,我的任务就是先去帮奶奶占位置。那时,茶 馆点的还是煤油灯,这种灯有三个灯嘴,吊在空中,把茶馆照得很亮。 老虎灶上,四五只大铁壶“嚯嚯”地响着。这种铁壶的嘴很长,茶馆 人多,伙计隔老远地把茶嘴递过来,不会有丝毫溅到外面。茶客们只 需付出比平时多五分钱,就可以听说书了。因为我占位置的功劳,奶 奶还会额外花两分钱给我买一两胡豆,让我慢慢嚼。说书人一般都会 多种口技:兵刃相交声,战马嘶鸣声,小儿啼哭声,浆橹声,家禽声 ……不一而足。同时,说书人还分饰几角:一会儿王爷,一会儿家丁, 一会儿小姐,一会儿丫鬟,惟妙惟肖。一次,我怀疑那位中气十足的 说书老头一定在桌子下安了什么机关,悄悄地爬过去,掀开桌布,一 看,那说书老头原来穿的是只烂布鞋,大指头露在外面,随说书的节 奏,一翘一翘的呢。呵呵。 话扯远了,回过头还是说看川戏。 后来,松溉有了电,又将原来兼演戏的市场盖着了电影院。于是 大家就叫嚷着,希望松溉能组建自己的川剧团。于是就公开招收演员。 一连招考了好几夜,有一天我和奶奶去看考试的情况。幕后响起一句 很亮的唱腔,锣鼓响起,一人甩着长“袖”(实际上他穿的只是普通 的乡下服装,并未着戏服,那“袖”是虚拟的),度着方步出来。大 家一看,哟,这不是方四吗?我指着台上喊:“奶奶,我认识他,我 认识他,他是方四哥。今天早上我还见他担粪呢。”众人哄堂大笑, 本来严肃的气氛一下子热闹起来。方四哥有点不好意思,但还能稳住 阵脚,有板有眼地唱完了一段戏文。 后来,松溉镇便有了自己的川剧团,方四哥也在内。剧团不光在 本地驻场,也到外地去巡回演出,很是火了一阵。但电影逐渐丰富起 来,连外国人亲嘴的片子都有了,电视也进了小镇,看川戏的就越来 越少了。大家说,川戏听不懂。于是剧团弄来幻灯片,破天荒地在舞 台侧面弄块白布打起了同步字幕。那字是剧团的王老师手写的,很模 糊,稍远一点就看不清楚了。而会认字的几乎都不爱看川戏,看川戏 的却又几乎都不识字。新鲜了一两天(大家冲着字幕去的,都没见过 打字幕的川戏呢),终于作罢,把幻灯机低价卖给了镇中学。 这期间,剧团倒是出了一条新闻:方四哥勾引有夫之妇被人家逮 住,赤身裸体给绑在街头的一棵黄桷树上。半夜,他挣脱绳子,偷偷 跑出了镇子,这以后我再也没见着他了。那个被偷的女人被丈夫爆打 几顿后,还是照常过活,见人也还是笑。 后来,剧团的人走的走,散的散,终于无疾而终了。 奶奶没戏看了。值得安慰的是,爸爸给她买了台录音机,她可以 整天听川戏了。磁带录的都是名角,奶奶却觉得不是那个味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