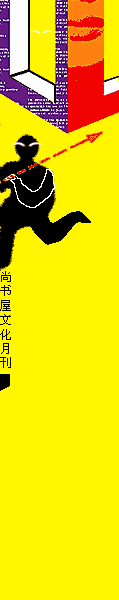
|
逃走的水车 修
竹
|
|
村南那架水车是什么时候逃走的呢? 许多年它与一座叫碓房的大木屋捆绑在一起,与一排包着铁皮的木杵捆绑在一起。就像一头驴,每天都与沉重的石磨捆绑着一样。 实际上它就是一头驴。只不过它操劳在南方,也不像驴那样需要吃喝拉撒。但它们干的都是同一种活。它们来到这世界上的使命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帮助人类消灭那些叫着粮食的植物。 驴被蒙上眼睛拉动石磨的时候,也像水车一样总觉得已经走出很远很远,它们不知道自己实际上都还在原地打转吗? 我离开这个村庄二十年,我走的时候水车还在它的老地方转着,它还和碓房绑得紧紧的。等我回来的时候,它却逃走了。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在我们村庄,碓房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场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村里人总在碓房里进进出出,你不时能听到木杵捣米时的撞击声。特别是到了秋收之后,碓房内外摆满了一萝萝黄澄澄的新谷,一个个高挂的木杵被解了套,它们被碓房外的水车所带动,起起落落砸向地面的臼穴,发出一声声沉闷的轰鸣。不久,谷物的糠皮被分离出来,而那白灿灿的稻米,被满身粉尘的人们挑回家中贮存。 碓房和水车,就这样构成我们村庄的一个部份,和一村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知道村里人是不会轻易放走它们的。不知哪个年代,是谁在碓房边种下一棵皂夹树,在我记事的时候它已长得高大而粗壮。那时我觉得这棵树就像一个忠于职守的卫士,它用浓厚的树冠把碓房牢牢地系在自己的阴影里。 还有那个守碓人二爷,他成天粉人似的在碓房里忙碌,像一把木杵一样弓驼着背,与碓房中那堆吱呀乱响的简陋机械混在一起。他无论往碓房哪里一蹲一站,都恰到好处,都天衣无缝地铆接在那里,成为碓房任何一组机械的一个部份。守碓人二爷就像一粒钢铢,被准确地安装在碓房这个大转盘里,他一辈子的行走都在碓房与水车之间。没有谁会相信,二爷会走着走着就把整整一座碓房连同水车给走丢了。 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村南。站在老宅的门洞,沿着河往上游望去,可以很清晰地看见那棵浓郁的皂夹树和树下陈旧而结实的碓房,看见黑黝黝的水车像个巨轮,在明亮的阳光下缓缓滚动。多少年,它咿咿呀呀的喘息声在我记忆里经久不息。
也不过二十年,等我回来的时候,水车真的不知怎么就不见了。 那座结实的碓房也已不翼而飞。 我童年的老水车,难道还真成了一头驴,终于挣开朽蚀的绳索跑了?甚至,还拉走了整整一座碓房?那情形该像一辆无人驾驭的驴车,只是又有谁会知道,它究竟在岁月深处哪一条路上急急奔走呢? 弄丢了碓房和水车的二爷,不知何时把自己也给弄丢了。空空的河边而今只剩下二十年前的阳光依旧。 我儿时常去的渠岸,现在已经倾废,我看见坍塌的渠道长满青草,昔日急湍奔腾的渠水,如今只能在茂盛的草丛间汨汨淹流。原来的碓房,现在成了一块荒地,杂草间露出几段倾颓的墙基和几堆破粹砖瓦,让人隐约可以猜出这里曾经有过一栋建筑。当然还能看见那棵皂夹树,如今孤零零地站在那片荒草地里,它浓密的树冠被闪电劈去了一半,因此显得苍老和憔悴。 这棵老树,它为之坚守一生的东西都已丢失,它站在这片废墟上还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一个人,怀着一个梦想生活,他为此游荡了一辈子,当他自认为已走过生活所有的角落,可以满载而归的时候,却发现不知何时丢失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 现在那个人就站在一道废弃的渠岸上,怅然凝视阳光下一地青草。他的心事也像这青草一样蓬勃而杂乱。他离去二十年,二十年让许多东西变得面目全非,甚至,那架牢牢拴在记忆深处的老水车也滚走得无影无踪了,那咿咿呀呀的喘息声已在寂静的时光里悄然消散。 我知道那个人终究也将逃离,像那架水车,最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捆绑住他。 只是,他能逃到哪里去呢?在漫无边际的岁月里,他不过也是一架最终要朽在路上的空驴车而已。 也许那时他将重新找到那架水车,它就散落在离他不远的地方。 2001年7月2日完稿于浦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