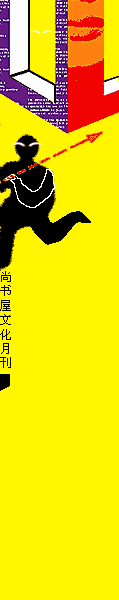
|
无人领取的邮件 扫红
|
|
在哪个偏僻的乡下邮所里,一定静静的躺着一封邮件, 很多年了,无人认领。 我坐在最前面铺了红台布的圆桌前,占最好的位子看表演,听他们唱卡拉OK。今天是HF公司十一周年,也是公司老总六十一周岁的生日,公司在厂房前的大操场上宴开数十围,上至老总,下至门卫,一起举杯。我是个嫁进来的亲,同了一些嫁出去的戚团团坐了,指指点点,呼喝小孩子,齐齐站起身高声说:“埙哥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啊!”埙哥亮晶晶的白头发下一张笑脸,身后一大群人干了一杯后又转去另外一张台上,觥筹交错,良辰美景。 早知道他们在宴后会有员工卡拉OK比赛,想也不过是:“妹妹你往前走噢噢”之流,大嫂是个爱脸逐流的尖刻人物,喜欢让员工搞些出风头有面子的活动,然后别过脸去撇了嘴说:“这些工仔……”她要的是体谅员工慈祥善良的老板娘的名。意外的是,在卡拉OK比赛之前,她们还请来了一个正儿八经的歌舞团,演出了一场很有专业水准的演出。音乐响起来,前来喝酒的临近一家工厂老板拍着一位主管的肩 :“叫他们不要加班了,都出来看看吧!”颇有大赦天下之意。演出很精彩,宴后的员工自然的从后面围上来,形成一个圈,最前面蹦蹦跳跳着鲜艳的孩子,他们无一例外的跟埙哥有着远远近近的血缘关系。 我剥着龙眼往小男孩嘴里塞,侧了头用粤语给旁边的人说:“这些打工的,说不定从来没这么近的见过真人表演呢。”旁边人瞪了兴奋的眼:“真係?”然后啧啧的回了头去看身后企企坐坐的工人。他们的快乐是真的,虽然快乐的源头有个那么功利的老板娘。如果功利能带来如此真实的快乐,为什么不更加彻底的去享受它?演员们退场后,员工卡拉OK开始了,他们的歌喉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唱歌时的自若,也打破了我的想象,我以为,这些来自乡间僻壤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会尖起喉咙,站在上面一动不动的望着屏幕,或是吐着咸咸的广东话,模仿歌星,做一些怪怪的动作。他们没有。我算算时间,是我停留的太久,还是现在的打工仔早已不是过去的打工仔?脚下蹦蹦跳跳的小孩子,拿着塑料花,不停的献上去,然后等他们下台后钻窿钻隙的把它们要回来,再献给下一个。他们全都是这些年里眼看着从无到有,一点点爬起来的,我的小男孩,也在里面跟小妹妹们抢着花,要最大的一朵,跟其中最大的一个男孩埋着头打架。我把他叫过来,大声数落他,逼他去说对不起,自己也明白这声对不起更多的是说给大男孩的妈妈听。 小男孩垂着脑袋说完对不起回来,我剥了龙眼熟练的往他嘴里塞,这一刻我又感受到自己,一个愈来愈顺手的角色,看不出半点嵌入的痕迹,在适当的位置做着适当的事,一个水乳交融挑不出错又不起眼的小妇人。我以这样一种方式淹没着自己,令自己看上去跟她们一样,似乎在跟自己赌着十年前的一口气:我就不信不能这么过一生!他的嘴在什么地方,看也不用看的把手一抬,龙眼就进去了,熟悉的岂止这些,一言一行,我可以不用再掩饰,混在她们中间,谁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两样。可是,她们不会在欢笑时忽然跳出意识来,由上而下的观照自己,看到一个人在一群人中间,穿着一样的衣服,发出同样的声音,那一个人,和一群人一模一样! 七月里一个人去旅行,好象重重帘幕里伸出一只手,往外深深的抓一把,我对自己说,要去透一透气,我知道一次这样的旅行可以让我在以后很多沉默的日子里继续延绵,我会找到一些可以让心灵驰骋的空间。丽江去中甸的路上,看不尽的山,我把手伸出去,五指张开,车一路颠簸着向前,我的手好象抚摸着对面的山,这些山亲亲近近的在眼前,手下,山河壮丽,还有什么可以跟它比?还有什么值得我花了心思去斤斤计较呢?我把眼睁得大大的,要看它们,把它们收到眼底心底,这一刻我在其中,我得到。 去迪庆之前,对它没什么印象,甚至连听闻都没有,我只是要找个地方走走,东也行,南也行。来到了,才发觉如此开阔,辽远,这些感觉不是来到了中甸后一下子涌向我的,是连续几天山山水水不停的孕育,而在心底逐渐辽阔起来。想到回南方后,依然要过着挤公车,赶时间的日子,但天地山河草原在这里,它们和我在同一个时空,与我并存,这种辽阔壮丽,浸入我心的最底层。不管我走在任何地方,发生任何事,它们都静静汹涌的在这里,和我并立着,陪伴我,还有什么值得我旁顾啊!我庆幸自己出来时既不邀旅伴亦不带相机,一切进入我的眼,印下来,见的那一刹那深深领悟,体味,无外念,无杂念,绿啊!辽阔啊!它们从四面八方浸入我的身体,我还想怎么样呢! 穿衣吃饭,我要安定的去过该下的日子。 台上的歌声悠扬,一曲《北国之春》,不太高的男孩拿了麦克风站在台上,他怎么想起唱这首歌?少年时期我们都曾唱过,可它过去的太久了!或许台上站的早已不是男孩,而是一个男孩的爸爸,可是怎样呢?他今晚站在台上唱的那么投入,放开歌喉,那么好的嗓音加上麦克风伊伊扬扬的飘送出去,不远处是影影叠叠的荔枝山,大片被征用后荒在那里的耕地。亭亭白桦,悠悠碧空,我是深深的受感染了,歌声把我带起来,从夜里站起身,杳杳的,杳杳的看出去,在偏僻的,不知名的什么乡下,一个邮政所里,静静的躺着一封信,很久很久,没有人来领取,或许根本没有收信的人,一封邮件,就这么静静的躺着,等待,或者不等待。 为什么我无法投入,身边的歌声与欢笑那么真实。小男孩拉着衣襟急急的踮起双脚,说要嘘嘘啊,要嘘嘘啊,这是我至亲的人了,为什么一霎那我会突然清醒?空空的盒子,我如空气般逸在里面,无人领取的邮件,静静的躺着。年年月月,我要这么过下去,谁也看不出痕迹,所有的足迹止于心灵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