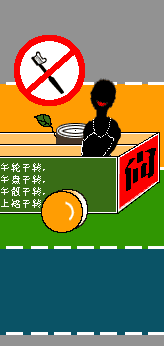
|
不完整的午睡
林filsy
|
| 很多时候,是住所选择了它的房客。在城市的某些地段,往往聚居着类似的人群。他们都是受到这些地区的房屋的召唤而前来生活的。
当然,因为是人的缘故,奇怪的事情总是会不断发生,并且那些当事人也会有那么一段日子显得与众不同。因此所谓人群的类似,只能说是某种程度上而已。 在我居住的地方,每天中午必然有一班不管别人死活的乡下人操着异常嘹亮的方言在楼下大声唤着某人的名字。有时我被迫从午睡的梦中醒来,听着他们肆无忌惮的呼喊声在小区上空回荡,而且那声音似乎永无落脚的地方……。 这时我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走进浴室,把头浸泡在装满凉水的铁桶里,任由冰冷的液体把耳朵塞得严严实实。我清楚自己是无从抗议的,因为几乎整栋楼都是他们的人, 除了住在隔壁的一对老夫妻之外。这帮外地来的传销人员象蝗虫一样占据着廉价住宅建筑的大部分孔穴,他们的存在使得这栋陈旧丑陋的七层楼房迅速进化成为城市里最肿胀的部位之一。 对此我当然是毫无意见的,我只是对他们吵醒了我的午睡而生气。要知道我在夜晚是从不做梦的,所以午睡就成为进入梦乡的唯一途径。而且,如果在礼拜天不用加班的话,我就会用整个白天的时间睡眠,这样才能有足够的力气把一个星期以来的梦集中重演一次。我会在周日的梦中分析过往的梦境里哪些细节出了错,哪些内容不够详尽,然后一一记下来,以便在下周的梦里做出补充。 做梦在我生命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就如飞翔之于候鸟、远行之于马可.波罗,与他们相比,我只是原地的旅行家,可我一样穿越了世界。我喜欢在光明的地方进入沉睡,我会想象着自己如何在日光下化成一座静默的石雕,倚在年迈的柱子上就象阿加门农王宫大门顶端那沉寂的狮子,然后欢喜地抛开生硬的躯体奔向奇异的世界。 有一次我梦见自己是一只昆虫,因为在聚餐集会上咬碎了同伴的头颅而被追缉。我在草叶和藤条做成的路上飞奔,各种怪异的眼睛在四周的树叶上飘浮,偶尔我还必须低身闪躲青蛙的巨大的舌头,以及一些毛虫臀部蠕动的尖刺。可是无论我跑得怎样飞快,同类的聒噪声总是在身后不远处跟随着。我来不及奇怪它们是怎样避开那些巨大的青蛙舌头的,就已经跑到一条午睡的蟒蛇的腋下,在那里我找到一片闪闪发亮的鳞片,我揭开鳞片发现一个细小的黑洞。我顺着那黑洞爬了进去,柔软的肉体立刻将我包裹起来,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推向某个方向。 我无力挣扎,窒息和恶心一阵阵袭来,我甚至听到了自己背上的硬壳破裂的声音,然后眩晕如期而至,那几乎是我生命里最艰难的时刻。一瞬间,我甚至开始对做梦本身感到绝望了。可是随后另外一种声响拯救了我,那是一首忧伤的吉他曲,带着些许日暮乡村的气息。我发现自己到达了蟒蛇身体的另一端,那里坐着一个醉醺醺的水手,他的一只腿已经被蛇的胃液消化了。可是他坚持坐在那里,手中抱着一把无弦的吉他。 他的嗓音沙哑,语调低回。“有一次你在这架梯子上放慢脚步,在太阳的光圈上盛开出玫瑰,你泪眼朦胧,仰望着天穹……” ,当这首歌唱到一半时,他的另外一只腿已经不见了,我看见他的眼中泪光涟涟。接着他的腰部也开始消失,然后是胸部,那歌声却依然在黑暗中回荡。旋律是如此忧伤,我不由听得痴了,呆呆地站在那里直到吉他声嘎然而止。我抹了抹眼中的汗水,我是不会哭泣的昆虫,流汗就是我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我最后看了一眼那歌唱的水手,他坐着的地方只剩下那把破吉他和一个未被消化完的喉结。 随后我钻进那吉他的腹部,在这安静的所在我回忆着自己匆忙的一生。从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开始,直到另一个星光黯淡的夜晚。我发现生命里除掉捕杀猎物的时光外并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创造,闲暇里我唯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静静地伏在一片树叶的背面仰望那无穷无尽的穹顶,我用触须感知它的存在,当我舞动柔软的器官去摸索它的面孔时,我知道它也在抚摸着我,这亲近使我激动得浑身颤抖。只是我的闲暇实在太少了,我的生命就在追杀与被追杀中度过。穹顶,只有穹顶,只有它宽容地看着我的生命热烈地烧成灰烬,无数的星光曾经祝贺我的到来,如今它们黯淡,或许是默送我的离去。它们就象我的兄弟姐妹,那些光华四射的瞬间总是伴随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到来,仿佛一场特别的仪式。 我躺在那破旧的木匣子里,伸展着触须和六只胳膊。等着这一生中最后时刻的到来,老实说我已经知足了,对于我这样一个已经疲倦于成为生存赢家的虫子来说,能够在死去前听到这么优美的音乐,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这是我充满杀戮的一生里最美丽的时刻,我本能地感到自己已经躺在了一个巨大的螺旋阶梯的出口。这个出口的背后是那无穷无尽的穹顶,那个容许我这卑微的生命艰忍地生存至今的穹顶,我能听到它轻微的呼吸-----当风声刮过蛇的脊背----世界在和应着,我在黑暗中听到了它们的歌唱,于是我微笑着,进入了沉睡。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仍然躺在那吉他里,确切地说周围有一堆蛇的粪便。我伸了个懒腰,慢慢从吉他里爬出来,小心翼翼绕过那堆蛇粪,爬到一块岩石下。我在那里匍匐了好一会,直到确定四周再没有那些追杀的仇敌。这时天空中下起雨来,岩石的前面迅速积了一泓水,我正好渴的厉害,就趁机想喝个饱,我把嘴唇凑到那片汪洋的前面,忽然大吃一惊。水中的倒影里竟然看不到我的模样,只有一个醉醺醺的水手忧伤地看着我,他的眼中泪光涟涟。 我惊慌地跳起来,来回地在森林的空地上奔跑。我找不到自己的触须和另外两只胳膊,背上的硬壳也消失无踪。我忽然强烈地想要发出声音,我想呐喊,却惊奇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到,我想起了那个歌唱的水手的模样,哦,人类的模样。随后,我想起了那个没有消化完的喉结,哦,人类的喉结。 然后我迅速地跑回岩石处,我在吉他周围的蛇粪里搜索,我还不习惯没有触须的生活,虽然我捡起一根棍子,却依然显得很笨拙,人类的手虽然看上去很灵巧,但是它不能象触须那样感知空气里微小的震动以及温度和水分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它不能象触须一样跟我最景仰的穹顶交流,手是不能听到天空的叹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