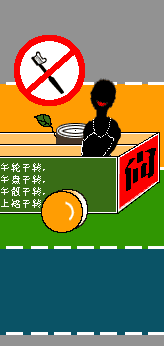
|
报屁股:从大学到小学的“鲁学”
十红一灰
|
|
中国有一门学问,叫“小学”,现在叫文字学,清朝最为流行,当时被称为显学,读书人大部分沉浸其中,其乐无穷,有一个”乾嘉学派”,影响了中国文化二三百年,就是“小学”的大本营。同时还有一个词“大学”,却是一本书的名字,影响了中国文化1000年。《大学》是儒家基本经典《四书》的第一部,是宋朝的朱熹从《礼记》里挑出来的一段,只有几千字。《大学》是相对于“小学”来说的,《大学》的第一句话“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就一下子给读书人提出了三条要求:探索世界的发展规律、启蒙、道德的自我完善。
清朝的乾嘉时期,是“小学”昌盛的时期,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中国文字学的黄金时期,却也是中国文字狱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文字狱,采用的是文字学(小学)的方法,从某个人的书里找出一句话,解释一通,牵强附会,用一个庞然大物的标准衡量一下,看看超出标准多少,然后定罪、抄家、杀头、灭族。如果把这种方法拔高一下,其实就是用“小学”的方法,假借“大学”的标准,对文人进行一次大清洗。 清朝之后,治“小学”的人少了,当时的学术界流行启蒙,流行救亡图存。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当时最显赫的人物应该是鲁迅,因为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都要学习鲁迅的道德文章。课本中的鲁迅,用《大学》的标准来衡量,简直就是一个读书人的楷模,对世界的不停探索、启发民智、崇高的道德,都是按照《大学》的要求来做的。然而,这里面就有了问题。从小学开始,老师就教育我们,鲁迅是反封建的斗士,《大学》是封建糟粕,鲁迅怎么会按照《大学》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答案很简单,鲁迅没有用《大学》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他是个聪明人,不是笨神,没必要把自己供起来。把他供起来的人是后来者,是研究“鲁学”的权威们,采用的方法也是老套,寻章摘句,从《鲁迅全集》里找出一些话,往一个庞然大物的标准上套,削足适履——这种方法,就是文字狱的方法。对鲁迅的高标准严要求,从本质上说,和杀他全家没啥区别。 一般来说,有三顶帽子(也可以说成三座大山、三个光环)套在鲁迅头上,“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鲁迅只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袋,帽子太多,额头冒汗还是小事,重要的是累弯了腰,脊柱变形,次要的是让别人没有帽子戴。这几十年来,靠鲁迅吃饭的人车载斗量,却没有一个人对这三顶帽子提出异议(顶多有人背后嘀咕一下),根本原因在于,鲁迅的帽子越多,他们可吃的饭就越多。举例,把鲁迅的思想家的帽子拿掉,研究鲁迅的哲学和思想史的人就要失业。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当然要护住鲁迅的帽子。 但是,毕竟已经有人对鲁迅的帽子不满了,也已经有人开始研究鲁迅的文学了——三顶帽子里,只有文学家的帽子严丝合缝。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他的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小说上(所谓杂文,现在看来,不过是两种用途,一种骂人,一种骗稿费),三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前两本研究的人多,因为容易和鲁迅的“革命家”帽子、容易和启蒙挂上钩,《故事新编》研究的少,因为里面充斥着怪力乱神,和唯物主义有点不对付。然而,《故事新编》恰恰是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真正体现出了小说的空中楼阁的特点——小说就是幻想,不是反映现实。 手头有一本《被照亮的世界——〈故事新编〉诗学研究》,就是研究《故事新编》的最新著作之一。现在的文学研究,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文本研究,一个是归纳中心思想。前者脱胎于西方的“新批评”,后者脱胎于中国的小学生语文教育。所谓文本研究,就是只看作品,细读作品,读出意义和味道出来(类似于中国古已有之的“小学”),而不是先竖一个标准,然后把作品往里面套,却又把标准说成是自己归纳出来的中心思想。《被照亮的世界》采用了部分“新批评”的手法,开始着重研究《故事新编》中的戏拟、隐喻、结构、叙事技巧,以图读出文本背后的意义。虽然还有着生涩的地方,却也算得上是“鲁迅文学研究”的先行之作——悲夫鲁迅,去世后将近70年,才开始有人研究他的文学,而不是研究他的革命和思想。 《被照亮的世界》采用的方法和结果,如果用小学大学套一下,则是用“小学”的方法,把鲁迅从“大学”里解放出半只脚——忽然想起来另外一个意义上的“大学”,高等学府。鲁迅一生教过的大学很多,估计全国许多大学里都有他的纪念馆。刚刚看到最新一期的《南方周末》,里面提到厦门大学的鲁迅纪念馆是该校著名的三大馆(虽然鲁迅只在这里呆了4个月),还有一篇专门的“斗士式文章”,着重讲了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的生活(实际上,鲁迅在中大只呆过9个月,主要任务和成绩就是把许广平泡到了手)。提到那个时期的中山大学,有一个人不能不说,史学大师顾颉刚,鲁迅的死对头。中大的文史研究,从顾颉刚起打下根基。只不过,现在没人记住顾大师,而是只记住“鲁三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顾颉刚学问扎实,因为用“小学”考证大禹的身世,被鲁迅在《故事新编》里损了一顿,从此成为文坛笑话——两个文人吵架,动用刀笔,纯属正常。可是,当鲁迅成为“鲁三家”,更多的人跟在鲁迅屁股后面也想“成家”的时候,史学大师顾颉刚就变成了“拉圈子、弄手段”排挤革命家鲁迅的小人了——“拉圈子、弄手段”这个词组是从《南方周末》上的文章里引用的,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