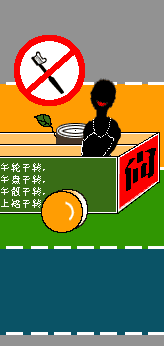
|
广州书情——回忆中的悲凉和回忆中的吃
十红一灰
|
|
九月已尽,秋风将至。古人经常说,秋令进补。所谓的进补,其实不过是个借口,从前不是现在,进补不是天天吞大力丸脑黄金,而是食、补不分。也就是说,在秋天要经常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贮藏热量,平衡内分泌,为漫长的冬季打下一个好基础——归根究底,还是因为嘴馋,想吃点好吃的。
而九月,恰恰为这种“进补”的思想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寻常来说,秋季是一年的收获季节,高粱玉米地瓜土豆自不待言,都是家常粗饭,上不了台面。对于文人雅士来说,秋季是“大快螃蟹”的大好日子,菊肥蟹黄,有的吃有的看,两下都不闲着,因而,“暮春招妓,初秋食蟹”成为了历代文人寻欢作乐的坐标。而对于梁山好汉们来说,秋季肥羊下圈,北雁南飞,正是大块吃肉、跑马溜狗的好时光,羊肉性热,佐以三碗烧刀子,赤膊下山,打家劫社,何等爽利! 广州人喜欢吃,因而,九月的广州书市,关于吃的书,琳琅满目,目不暇接,让读者垂涎三尺的同时,陷入了一片大块朵颐的幻象之中。在诸多以吃为旗帜的书里面,有三本书比较突出,不能不提出来示众。一本名叫《多味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8月版),是本吃的散文合集。这本书,关键不在于吃了什么,而在于是谁在吃。“多味斋”是《人民日报》副刊的一个栏目,已经有许多年头,经常在上面的溜达的人不是耆老,就是墨客,或者兼而有之(单看作者,萧乾、陆文夫、于光远等等,或者名文人,或者名吃家)。这本书就是这个专栏的一个小总结,从专栏中挑肥拣瘦,去芜存菁,宛若“择菜”,精挑细选出了将近百篇文章,汇总成集,可谓色香味俱全。 广州地处粤地,火大,对于秋的悲凉不甚了解。近现代文人,一提到秋,莫不想起失意的北京,想起郁达夫的名篇《故都的秋》,回忆中的悲凉和回忆中的吃,最是伤魂魄。三联书店最近出版了赵珩的《老饕漫笔——近五十年饮馔摭忆》,正是回忆中的北京和回忆中的吃的记录。我对作者的生平不甚了了,然而该书由王世襄先生题签,朱家缙作序,二人皆是北京老玩家,这本书的分量可想而知。翻开书本,所说的虽然只是中山公园的藤萝饼和致美斋的焖炉烧饼,却都属于过眼烟云,足以叹息。在广州读这本书,正正符合了“万里悲秋常做客”的心境。 还有一本名叫《好吃——食物与文化之谜》(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7月版,作者美国人马文·哈里斯)。现今是文化大膨胀的时代,吃,不仅要吃出档次,而且要吃出文化,方能称为会吃。然而,吃简单,文化却难,因为文化一向被文化人垄断,正如同食物的美味被舌头垄断、文化的精妙被嘴皮子垄断。这本书恰好缝合了舌头和嘴皮子两个领域,使吃与文化合而为一。 闲言碎语,没有离开吃字,似乎九月的广州书市,除了吃没别的,其实不然。在小说方面,唐浩明的三卷本历史小说《张之洞》(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甫一上市,便占据了书店柜台的显要位置;曾获“茅盾文学奖”的作家阿来,乘着文学奖的东风,不仅书卖得好,而且出版了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目前广州书市,仅可见到文集中的两卷(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中短篇小说集》)。 在这同时,法国的新锐“美女作家”玛丽·达里厄塞克的新书《幽灵》、《晕海》悄悄地由海天出版社推出(书的版权页标明是2001年10月版,广州书市属于“提前到货”)。两年前,达里厄塞克的《母猪女郎》中文版问世,和当时正红的中国版“美女作家”一对照,高下立判,美丑分明。相对于中国的“美女作家”,达里厄塞克的意义有二:作家不仅要会秀,而且要会写;杜拉斯已经老了,现在流行达里厄塞克——最关键的还是后者,足以让抱着杜拉斯睡觉的中国“美女作家”们摔一大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