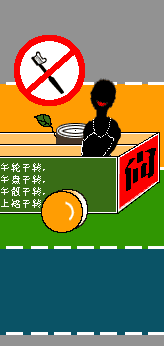
|
卡夫卡的打字机
马牛
|
| 本世纪初叶的一些夜晚,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只要你睡得足够迟,都会从寂静中听到一种轻微的叭嗒声。叭嗒声有时急促,有时迟缓,急促时像一头轰轰走来的食肉恐龙,迟缓时则像摇篮旁年轻饱满的母亲有一声没一声的吟哦。有时叭嗒声会突然停下,久久地沉默,像是很丧气,如果你是那些夜晚忠实的听者,此时你能听到的,只是引起自己身体不自觉轻微摇晃的心跳。
很多人想知道那种叭嗒声从何而来,他们向认识的亲友打听后一无所获。第二天夜里他们又会迟迟不睡,等候叭嗒声的到来。通常这时它都不会来。它每天来的时候都是他们快要睡着的时分。先是轻轻的一下,两下,让你不敢肯定还会听到第三声。因为它毫无规律可言。可能接下来的马上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将整个夜晚袭卷,也可能像雨后屋檐上滴下的雨水,整整一个夜晚都保持一个不紧不慢的敲击速度。 我假设你是相信奇迹的人,我告诉你,本世纪初叶那些回响在深夜的叭嗒声,是年轻的卡夫卡在打字。 卡夫卡笨拙的打字机里,藏着一个忧郁得让人发指的魔鬼。这个魔鬼,我管它叫卡夫卡一号。它与卡夫卡同时诞生,同时长大。在卡夫卡成长的岁月里,它时常借助一些雨天或姑娘,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每个人都需要时不时证明一下自己的存在。
终于一天,卡夫卡买了打字机。他坐在打字机前,一天也没打出一个字。他摸摸这儿,敲敲那儿,以确认买回来的是一架真的打字机而不是汽泵什么的。当天晚上,他开始用手指敲击键盘,他先打出一个A,紧接着不费吹灰之力就打出了24个字母,他对自己的手指很满意。但当他想打一个单词那单词却迟迟不出时,他烦噪了。新故事开篇的几个句子一直在他脑子里转,可他一个单词也打不出。他在房间踱来踱去,他想到过桌子上放着的纸笔。但他现在已经不屑于用它们了。他把衣服一件件脱去,重新坐到打字机前,闭上眼睛。
卡夫卡一号冲出卡夫卡身体,跳进崭新的打字机,是在凌晨五点。它在卡夫卡体内,把自己分解,通过卡夫卡的每一个毛孔,每一根发梢跑出,把自己像一阵风似地灌进了打字机。在打字机内,它重又把各部分器官重组,恢复原先的怪模样。 第二天,卡夫卡在打字机前醒来,阳光已经透过窗帘照到了他的臀部。卡夫卡的臀部很窄,上面除了早先就有的几粒发红的小疙瘩,还有就是坐了一晚的椅子压出的纹路。他穿好衣服,吃了早饭,买了一本教打字的书回来,重又坐在打字机前,他突然觉得身体空空的。他以为是早饭吃得过少,但早饭他吃的确实不少呀。又是因为什么呢?他身体里的一些东西被人抽走了,他不知那是些什么东西,但他知道他与它们相依为命已经许多年。 一个星期后,卡夫卡在打字机里发现了卡夫卡一号。 他把那个单词连打了三四十遍,还是没出来。他怀疑打字机出了毛病。他拍拍打字机后又打了一遍,还是没出来。他又拍了好几遍打字机试图打出那个单词,但历史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失败了。
卡夫卡轻轻合上机盖,用最微弱的旋转力,用最长的时间把那几个螺丝拧好,不动声色地开始他与打字机为伍的创作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