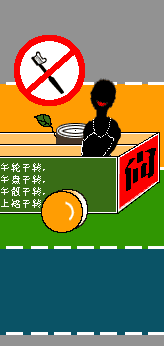
|
猫
湖中罂粟
|
| 去年的整个春天和夏天,我都在跟一个眉清目秀的矮个子男孩同居。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农村里租了一间阴暗潮湿的老房子,整天穿梭在狭窄坎坷的青石板小巷上。房东是一个肥胖到出奇的女人,走路的时候会发出类似打夯的声音。她眉飞色舞的跟我们讲着房里的那张大床,说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古董,她结婚时从父母那里继承过来的。
我挺喜欢那床,红木的,雕花,跟古装电视剧里的一模一样。而除此外这房子一无是处,老旧到高低不平的水泥地面裂开丑陋的大嘴阴笑着,石灰粉刷的墙上斑斑点点,让人联想到上个世纪的蚊虫尸骸。更要命的是无论如何洗刷都无法去除的那股腐败气味,一推开门就从衣柜里,床下面,抽屉里,房粱上密密麻麻的涌出来,几乎让人窒息。 我们想了很多方法让这房子“年轻”起来,我买了茉莉花香的清新剂没日没夜的喷,他借了小型音响放着HEAVY METAL音乐,然后我们就钻到黑漆漆的床上惶恐的作爱。说是惶恐很贴切,或者也可以说是淡淡的恐惧。我们通常先是各做各的事情,然后几乎同时停顿下来,同时感受到房子里的阴冷气息。害怕就这样跟它一样腐朽下去,于是选择了最激烈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他趴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恍惚看到房屋伸出无数的手臂挥舞着,叫嚣着,强烈的诉说着它对我们的不屑和厌恶。 我想我有必要说说跟我一起陷入到老房子的噩梦里去的人,或者还有必要谈谈我们之间的相识,相爱,如果爱情不那么让人厌恶的话。他实在是太标致的男孩子,被过于精致的五官拖累着,永远都是毫无生气,苍白单薄的。他身上长久的驻留着油腻的味道,那是奶油蛋糕上的雕花,是和路雪冰激凌上的巧克力酱,是漆黑的夜里快乐的呻吟。所以每个贪婪的女人都爱他。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洗头,身上的味道跟洗发水起了某钟奇妙的的化学反应,整个院子里都是有关暗示的风情万种。我心意摇曳。他微微抬头,露出白色泡沫下敞领的昏黄色衬衣,脸的部位是模糊一片。于是我跌跌撞撞的走出去,浑身血脉曲张,热辣辣的欲望烧刀子般在小肚子里淌个不停。 我跟他本来是同一家的房客,他住楼下,占了间宽敞靠阳的房间;我则要每天顺着长长的楼梯上楼,绕过房东的卧室,走到我那间装修讲究的小屋子里。这家人颇为有钱,新盖的楼房整洁明亮,楼上楼下共住着七八个学生。我是最新搬来的,恳求了房东太太很久她才同意让出房子。 你们男男女女住多了容易出事。她表情复杂的看着我,眼角带着种嘲弄的预感,好象我天生一副狐媚象。 结果没出三天就出事了。 那天晚上气候很好,小风熏人般恰倒好处的吹着,我穿了双软底拖鞋,悄无声息的下了楼。他房间的门默契地开了条缝,暗淡的灯光漏出来。 我找不到针线了,我来借针线的。我贴在门口,压低声音说,那语调我自己听来都觉得虚幻,好象水上的浮萍,没根没基的。 门喀的开了,声音小的出奇,我仿佛看到门后的他心照不宣的微笑着。 想想也觉得好笑,半夜了借什么针线,楼上还住着好几个女生呢,又偏偏来找男生借,他就算是白痴也该心领神会。 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深了,窗外连半个月亮也没有,我坐的越来越舒服,索性把双腿放肆的搭在床沿上。他根本没一点找针线的意思,悠悠的盯着我看,苍白的脸上一双妩媚的眼睛飘忽忽的好象洞悉了一切。 于是我就干脆跳到他怀里了。他用被子蒙住我的身体,钻过来解我的衣服纽扣,他的手酥软酥软的,好象云片糕。我就吃吃的笑…… 后来他反复的取笑我那天的样子,你他妈的真象个狐狸精。他说这话的时候用了不适合他的脏字,听上去就分外的真情外露,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在他床上窝了大半天,房东一家故意跟我们作对一样赖在客厅里不动,还唧唧喳喳的大声宣扬着他们的存在。我就再大胆也不好意思蓬头垢面的从他房间里走出去了。结果我们就那样小心翼翼的躺在被窝里。长期的倾听外面的动静,活活一对偷情的野鸳鸯。直到傍晚我才决定豁出去了,或者说其实是被尿憋的,我理直气壮的拉开门回自己的房间收拾东西,走过房东太太旁边的时候故意昂着头装做什么都没看见。 当晚我们就搬出去了,到了这个份上再赖者不走显然就不够聪明了。我一趟趟抱着东西下楼的时候房东太太就站在楼梯口冷笑着看我,眉眼上都挂着未卜先知的得意,嘴里嘀咕着她家的房子要去去晦气了。我想现在这时候自然开不了口要求退房钱了,突然就觉得她才真象只狐狸。老狐狸。 深夜的时候我跟他已经躺在阴暗潮湿的老房子里了,这样仓促的找房子还能在乎什么条件,何况这里的优势是明显的,独门独院的一间大屋带厨房厕所仅仅每月80块,好象白捡的一样。唯一令人不安的是那个胖房东显得过分热情了点,炫耀起自己的床的时候也有些古怪,可当时我紧拉着他的手,被所谓爱情或者肉欲一样的东西迷惑着,只觉得就算那床上盘踞着她家祖上十八代的灵魂又有什么关系。 一个人睡这种地方我非得吓死。我侧着身子,边说话边轻轻往他耳朵里吹气。 有我在怎么会让你一个人睡呢。 难说,要是万一哪天你跟朋友玩去了,我自己先睡下怎么办? 那你就放音乐,借本好笑的书看,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不行,我总觉得空荡荡的,不如我们养只猫吧。 于是就养了只猫,一个月左右大的狸猫,虽说瘦得蔫蔫的,也算是给房子多了些许的生气。很多时候我们陷入恐惧——情欲——疲惫——再恐惧——再情欲的怪圈子,常常旷整天课,在床上纠缠到一句话都说不出,只是面色沉沉地看着对方出气。猫就偶尔成了插曲,它从肮脏的角落里窜出来,赖在床上不肯下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恩爱的兴致。我们开始的对策是暂时停止动作,执著的一次次把它丢下去,后来连这点力气也没了,就任凭它瞪着发亮的眼睛旁观。 其实我并不太喜欢猫,我从小就被告之猫是奸臣,是见利忘义的典范,狗才是会忠心耿耿对你好的伙伴。但当我认为这间老房子需要一点活物装点的时候,猫就奇妙的成了第一选择。我想这都是因为神经衰弱。自从住在这里以后,我随时都是焦躁不安的,没有胃口,身体渐渐消瘦。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困到眼皮都搭拉下来了还是满脑子幻象。据我妈妈以往的说法这就是神经衰弱了,她生了我们兄妹几个后,开始天天嚷着自己神经衰弱,说都是我们让她太操心害的。长大后我就总念着那些神经衰弱的女人。她们总是很瘦弱,脸色苍白的可怕,穿着黑缎子的旗袍。头发也象黑缎子一样长长的飘下来。她们把自己整天的关在屋子里,一推开门通常都是中午时分了。她们支着雪白雪白的腿站在门口张望,眼睛却总是迷惘的空洞的好象什么都没看,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她们都爱养猫,爱把猫体贴的抱在怀里小心呵护着,比养孩子还亲。很奇怪我对于她们的想象是如此的无微不至,纤毫尽现,好象她们成堆的就在我四周存在着,一不小心就会碰到两三个人的衣角。可她们跟妈妈一点不象,所以我想妈妈是骗我的。我跟她们也不象,但我还是突然想买一只猫,假如我开始去疼它的话,我想我就真的神经衰弱了。 我并没有去疼那只猫,或者说我还没来得及去疼它的时候,它已经成了令人生畏的敌人了。它渐渐的不再象是一个可怜巴巴的附属品,一个依赖者,一个天生该低声下气的东西,而神奇的转变成这房子原本的主人,一个无所不知的神祗了。我相信这一定是在某个漆黑夜里进行的肮脏交易,房子里的那些腐败的源头化成某种有形体的东西收买了猫的灵魂,然后猫就跟它们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千方百计的想要我们发疯。 我的伙伴显然比我更脆弱些,有一天我们在床上躺着,到了该亲热的时候,他突然就阳痿了。我安慰他说没关系,任何人象我们这样没日没夜的做都会出差错的,他已经是万里挑一的精力充沛了。他丝毫不理会我,搭拉着眼睛发了会呆,好象在思考什么,又好象什么都没想。然后他就突然从床上跳起来了,赤裸着身体满屋子转。我吃惊的问他在干吗。他看都不看我的哼了一声,说,找猫。
这时候那猫就得意洋洋的从窗口跳了进来,它长胖了许多,浑身的皮毛乌黑发亮的,好象一只掉进油瓶里的大耗子。我恶狠狠的瞪着他,希望他知趣点滚开,它却偏偏快活的叫了几声,轻盈的一纵身就卧在床上了。男孩的眼睛里立刻发出温情的光彩来,脸上的神色又幸福又慌张,似乎比起我来,他更在意那只猫。我歇斯底里的尖叫起来,扑过去挖猫的眼睛,我是真的害怕。我发誓要杀了它。男孩迅速阻拦了我,他粗暴的把我抛到一边去,然后乐此不疲的强奸了我。这过程里我始终发出骇人的尖叫,撕咬着他的肩膀。而最后他的冷漠征服了我,我把头偏到一边去,清清楚楚的看到猫在笑,它淫猥的裂着大嘴,边笑边有白色的谗液滴下来。 我本来是决心要离开的,但我舍不得他,我想只要不走,总能想出点法子杀死那只猫,这样也许他就会好起来。但我从没想过搬走,我发现其实我已经爱上这所房子了,包括爱这里总是阴暗潮湿的气氛,这里腐烂的味道,这里晦涩的罪恶感。虽然我知道猫其实只是帮凶,真正的罪魁祸首就藏在房子里,津津有味的欣赏好戏。 天气不知不觉的就热起来了,我们更加的不愿意出门,因为房子里永远是阴凉的,好象跟外面隔了三十个纬度。我们买了大堆的超市食品堆放在墙角里,把饼干屑掉的满地都是。很快我们就发现那些食品在以可怕的速度腐败着,有时候一天过去就全部长出绿色的霉点来。我开始迷惑这房子是否存在着时间断层,一切东西都沿着另外的时间轴飞速向前漂浮着。于是我每隔十分钟就仔细的看一下镜子,观察自己面容的变化记录下来,结果是徒劳的,我既没有长出明显的皱纹也没有迅速憔悴枯萎。 我跟男孩的关系变的微妙,我们尽量避免交谈,亲热的次数减少到一天一次。大多数时间我们陷入孩子般的游戏中,我用了很多幼稚的方法企图伤害那只猫,而他毫不费力的一次次戳穿我。 我想你是爱上那只猫了。有一天我说。 不过你早晚会被猫毁了的。 不过我们都一样。我们是注定的。 我们不是在做梦吧? 我想我们很快会跟饼干一样长毛的,然后这房子就会把我们一点点吃掉。 我独自说了很多很多的话,说的口干舌燥,可是他始终一言不发。我只好拼命摇晃他的肩膀,他在我的手下好象布娃娃一样没有一点重量。我就松手,我怕摇坏了他。然后我知道他再也不会说话了。 又有些日子过去了,也许是几天也许是几个月,我对时间开始丧失概念。再后来就靠近了整件事情的结局。当时我难得的外出,在青石板小路上静静的走了一个来回,努力思考某些事情的关联,我认为一切显然是有预兆的,从我那个下午在院子里偶然看到他洗头开始,我们就掉进一个光怪陆离的洞穴里。我们好象两只实验用的白鼠暴露在解剖台上,任凭比我们强大的多的东西的冷酷观摩着。关于整个过程的意义我们却永远无法参透,因为超乎我们的理解能力,溢出我们的思维范围。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某种讯号,好象计算机程序里的中断响应般投影到脑海里。我就知道该结束了,我站在迷宫的出口了。我回到房子里去,看到他浑身都是浅浅的抓痕,猫已经死了,躺在淡淡的血泊里。我没觉得惊讶,平静的把猫的尸体拿到屋外去,挖了小小的坑仓促掩埋了。 第二天他病倒了,浑身的伤痕都开始加深加重,渐渐的腐烂下去,好象滚水浇灌下的冰。挨着伤痕的肉体沿着一定的方向融化在空气里,冒着白烟,发出兹兹的声音。没一会连白灿灿的骨头都露出来了。如果不赶快的话他会死的,我想。于是我背起他,急忙的朝医院跑,他的身体轻飘飘的,一点重量都没有。 到了医院我直接冲到急诊室里去,那里一共有三个医生,看见他都露出既惊讶又厌恶的表情。其实他已经好多了,伤口都不再腐烂,也不再冒烟,保持着椭圆的形状,整个人好象用蜂窝拼凑起来的玩偶。 怎么弄成这样的?一个女医生冷冷的问。她的声音实在是冰冷极了,一出口就冰棱一样往下掉。 他们更加惊讶了,很默契的交换了一下眼色。就有一个很好看的男医生从我肩膀上把男孩接到手术床上,而问我话的女医生快步走出门去了。我知道她是去打电话报警了,他们一定觉得我疯了。可我不能疯,我要把整个事情做完。 我只好回过头拼命的跑,他们在我身后大声的叫着什么,慢慢的听不清楚了。我一口气跑到马路上才停住。那天的天气真好,阳光是橘红色的,纯净的跟小孩子手里的蜡笔一样。树都长的很旺盛,叶子绿的好象抹了一层琉璃粉。柏油的马路刚扩建了,白色的斑马线都是崭新崭新的。行人也格外的年轻,似乎每一个都不超过二十岁,情侣们穿着光鲜的衣服,皮肤在阳光下滑嫩的跟大理石一样。我被这一切吓住了,把脑袋沉沉的低下来,拼命的藏到树阴里,好象一尾浅滩上的淡水鱼,可怜巴巴的晃动着破碎的尾巴。 除了那老房子我竟想不出还能到哪里去。我别无选择。 推开门我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房子里熟悉的腐败气息淡了很多。但我实在太累了,懒得去思考问题,只想赶紧躺下去。床上依旧是黑漆漆的,却赫然多了一个人。那是一个黑缎子旗袍的女人,头发也象黑缎子一样长长的飘在脑后。她的皮肤是雪白雪白的,神色是慵懒沉迷的,很高贵。我仔细端详着她,发现她长的很熟悉.似乎就是我常常惦念的那些抱猫的女人中的一个。我就觉得亲切起来,好象老朋友一样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对不起啦,你先让一让,我要躺下啦。 她很温柔的朝我微笑着,侧过身子坐到床角去了。 我摸索着上床,突然碰到一团毛茸茸的东西,起身一看,原来是那只猫!它依旧是神气活现的,如果不是胡须上沾着几粒泥土,我怀疑它压根就没死过。它朝我摆了摆尾巴,露出难得的友好样子,然后往靠床的那面墙上撞过去,一闪就不见了。我楞了楞,小心的触摸它消失的地方,发觉那里竟然是空的!手指头轻轻一戳,就穿过去了,好象弄破一张塑料薄膜。我把手朝里面深入更多,渐渐的整个小臂都探了进去。手指尖那些柔嫩的皮肤隐隐约约触碰到棉絮般的物质,软软的,暖暖的,有种难以名状的惬意。于是我想我不如就这样掉进去吧,象那只猫一样,至少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可惜就在这时候有人拉了我一把,我回过头,看到那个黑旗袍的女子。她贴着我的耳朵,带着几分暧昧的气息轻轻说,快跑。 她的声音真是说不出的婉转,听得我浑身都酥麻了,一心只觉得她是绝对不会害我的,就赶紧把手从墙里抽了回来。她又轻轻推了我一下,我就头也不回的跑出去了。我又是一口气跑到大街上才停下。天气还是那么好,行人还是那么新鲜,奇怪的是我却一点不觉得害怕了。我甚至把头昂的很高,我觉得我简直象个主宰者,我哪里都可以去。 过了好几天我才记起受伤的男孩,他的伤大概好的也差不多了吧,我想。于是我到医院去,询问一个被猫抓伤的年轻男孩住哪个病房。值班医生抬起他陌生的脸,说,猫抓伤的都不住院的。 我说,可他不一样,他浑身都烂完了的。你查一下,象他那样烂掉的人不多啊。 他看我的眼光更加奇特了。那你说说病人的名字吧,我帮你查查。他说。 我呆在那里,脑子里出现黑白电影的定格。我发现我或许是根本不知道男孩的名字,男孩并不存在,我杜撰出了他,日日意淫。那么老房子也就很大程度上可能并不存在,这让我怅然若失。。但也或者我曾经知道,但因为某种原因忘记了。这两种原因的理由都不够充分,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我疯了。关于疯了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这样事情就容易解释多了。你瞧,很多时候我们总还有条最后的路可走。 以后我再没见那间房子,不论是现实还是梦境。当然,猫倒是常常见到,它其实是一种很可爱的动物,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