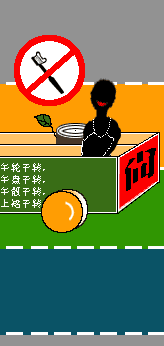
|
多些情节
浅绿
|
|
初见老何 老何到公司来找人,第一个接待他的就是我。老何穿着卡其布的外套,深蓝色布裤,解放鞋,夹了人造革的皮包呐呐地站在我面前。我的第一意识,又是一个来上访的老乡。于是起身给他倒了一杯水,复又坐下,静待老何发话。老何憋了半天,才吭吭地说:我找李玉其。 李玉其是我们这个小办事处的外事员,和我一个办公室。负责在外跑,联系政府与单位的协作,或者下基层去处理一些事务。老何说是李玉其的表叔,我打了李玉其的手机,李玉其在电话里想了半天也记不起这样一位表叔,我不耐烦地打断他:回来一见不就得了。这样,李玉其的表叔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静待李玉其。 这期间,我翻着昨天前天大前天的报纸,没搭理老何。老何闷头喝着水,眼睛瞅了我几次,似是想搭话的意思。报纸上千篇一律的每天不外乎奸杀、济贫、抓赌截娼。财经版也没啥好看,证券版更是看了心疼,这两天熊的一塌糊涂。翻了一圈,我放下报纸,递了一支烟给老何。自己先燃了,再把火机丢给老何。老何黑黑地脸上竟抹了一片红,说着:瞧您客气的,瞧您。接了过去,点燃,深吸了一口,嘿嘿笑了声问道:同志,您贵姓呀?我姓王,叫我小王就成。老何又笑了,脸上的皱纹拉平了些。他把椅子向我这边拉近了些,低声问:你们这儿就只管上访,不管别的?我笑笑:嗯,基本上是这样。视情况而定。喔——老何意味深长地应了声,没再回话。低头抽了两口烟,才犹豫着又问我:那,这文物是哪个部门管哩?文物?我脑中闪了一下,问道:怎么,你有文物?老何又嘿嘿笑了,小眼睛瞪圆,凑近我,说道:是我在路上拣的,好东西。说着他把手箍成个圆形,瓷盘,清代的。我脑中转了几个圈,这老何到这儿来找他侄子,完了是为个拣来的文物。这事儿,呵,有好瞧了。正想着,门被推开,李玉其挎着个包快步走进来。 叔侄相见,寒喧一番。我自觉地退出门外,到隔壁办公室找人聊天去了。半个多小时后,李玉其推门招呼我,说出去一趟。我这才回到办公室,看看时间,已经不早,整理了上周留下的一些事情,送了文件到打字员小周那儿,跟她开几句不疼不痒的玩笑。再回来时,李玉其已坐在我办公室翻报纸了。 见我进来,李玉其先笑着说:王哥,你猜那表叔找我啥事儿。我和李玉其关系一向不错,他是单身汉,宿舍在我家隔壁,我爱人没少照顾他。这会儿因着避嫌,我没提出老何跟我讲的文物的事儿。见我不吭气,李玉其又饶有兴趣地讲了下去:嘿,我那表叔说是居然拣了个文物,瓷盘,清朝的。喔?我微笑着:这倒是个大新闻。什么呀,我刚上他们家看啦,什么文物,整一个仿的,假的。假的?我疑惑着问。假的,明显的很,那盘底的漆字一看就是现在的油漆印。李玉其喝了口水:我这不懂文物的人都知道。正说着,下班铃打响,李玉其拿出饭盒,拉我去食堂打饭。边走边说到昨天那场足球,唉,那个臭的—— 查小梅 每晚上床睡觉的时间我们除了周末例行夫妻生活,平日都是做工作交流。一般来说她讲的多,我讲的少。这天是周末,我们吃完晚饭,小梅刷碗,我看电视。我知道小梅今天一定有什么好新闻要讲给我听,她就是这样,有让她兴奋的事儿时讲之前总是一声不吭,我若要问她,她反而瞪眼装呆。后来遇此情况我索性不理,由她自个儿故做神密状去。不消一会,她就会主动上前来说。果然,陪我看了会新闻后,小梅连她每日必看的连续剧都放弃了,匆匆催我上床。我依言上床,靠在床头看报纸,小梅夺过报纸,满脸神秘兴奋地对我说:老公,你知道我今天遇到什么事了吗?我揽过她的肩,随口问道:什么事。今天一个老头来我们报社说是拣到了一件文物,要求寻找失主。小梅语言简炼,这是由她编辑新闻的工作养成的。这项新闻由我具体负责,我还为这老头做了个专访,呵,这可是我从业以来最好的新闻了。小梅兴奋地两眼放光,脸蛋红朴朴的招人喜爱。老头是什么人呀。姓何,叫何东。家住城郊,挺穷的,平时靠收废品生活。何?我脑中一激灵,多日前上单位找李玉其的老何几乎被我遗忘了。我立刻来了精神,大致说了一下老何的外貌,小梅一拍大腿,是呀,就他,你也认得?我简单地说了那天老何来单位找李玉其的事,还说李玉其上他们家看过了,那是赝品。小梅沉思下来,说这事儿看来不能急急地登出,还需慎重,要调查清楚。我想这无非是个老头拣个瓷器,非当真品,想露个脸邀个功什么的。这样想来,就没往心里去。看看小梅白皙丰腴的身体,便拉下她轻声说:做作业吧。小梅嘻笑着欲推还休,像个姑娘似的。我就喜欢这她这点,扮天真扮地挺自然,不做作。 去老何家 第二周上班的时候,我对李玉其说了这事。李玉其一拍后脑勺,说:啊呀,这老何可真够折腾的,找上报社了。我没再搭腔,想着人家家的事儿还是少说三道四为妙。李玉其接了任务出门,我依然在办公室里接待上访群众。这是我们这个小办事处的职责,人不多,却管了整个城市一大堆的破烂事,下水道堵了、邻里纠纷、下岗工资拿不到、某机关办事不力踢皮球。我戏称这里是城市居委会,小梅有许多小道新闻就由此而来。下午正想休息一会,小梅来了个电话,说是她向主任反映了此事,主任要她下到群众生活中去,仔细认真地调查清楚。不管是不是真的文物,都是一个好新闻的素材。小梅说待会就去老何家。我笑说她的冲向新闻第一线的态度快赶上驻战事地区的战地记者了,小梅不屑地嘁了一声,懒得跟我说话,急急挂了电话。 我伏在桌上休息,脑中却反复地想到老何这事。想到老何穿着卡其布上衣,倨促地站在办公室门外的样子,再想到他挤着小眼,认真地说拣到文物,渐渐开始对此事有些动摇了,难道老何说得都是真的?正想着,李玉其推门进来,猛灌了一大口水,对我说:王哥,我刚在路上想过了,这事儿啊,保不齐是真的。要不,你下班陪我再上他们家看看。我正感着兴趣,就应了下来。回头给小梅打了个传呼,对娇滴滴的寻呼小姐说留言,下班晚些回家。 下班后,我和李玉其先到隔壁小饭馆一人吃了一大海碗三鲜面,抹抹头上的汗,骑车向老何家去。拐七拐八,上坡下坡,车子在快到市郊的地方停了下来,李玉其走前头推着车,回头招呼我:王哥,这路不平,也快到了,推上走几步。我应声,心里一阵后悔,大冷天的晚上跑这荒郊野外来。几步后,李玉其说到了。这是一间平房,属于违章搭建,蹲在小路的拐角处,极小的窗户里有光,门旁边堆了几大包用蛇皮口袋包扎好的废纸和塑料瓶。 李玉其喊了一声:表叔!停了半分钟,木门拉开,老何的脸背着光,不太看得清。老何眼神不好,看了我们半天,这才看出是李玉其。忙将我们让进屋。这是一间十个左右平方米的小屋,通气不好,屋子里气味有些难闻。都是极旧的家具,堆放墙角。我们来之前,老何正蹲在汽油炉前烧他的晚饭,让我们坐下后,老何拿了一只碗,从锅里舀了勺稀饭一类的东西,上面铺着青菜叶。老何有些羞涩,蹲在一边吸溜吸溜地划饭,三两口就划完了。老何擦擦嘴,接过我递去的烟,点着。李玉其先开言,说了一些老何居住条件不太好,问候他身体一类的话。显然老何对这些问题已经驾轻就熟,随便应付两声,句句说得诚恳。李玉其干笑笑后,直奔主题,说是想再看看老何拣的瓷盘。乘老何弯腰找东西的时候,我打趣着问是否今天有记者来采访他。老何又有些脸红,吭吭地说:是的。晚报的记者同志,问了他拣文物的具体经过,也顺便看了看。还说过两天带些专家来鉴定一下。 老何从床里的皮箱里拿出一个布包,好像是旧衬衫一类的布包,打开后,拿出一个瓷盘。已经被老何洗得很干净,釉色莹润似玉,造型独特别致,盘底漆了清光绪年楷体字样。我和李玉其对望一眼,李玉其指指盘底的字,我仔细看了一下,好像确是油漆漆上的,不像是从前印的火漆。我将瓷盘还给老何,老何照样将它小心包好,放回原处。我问老何:这个瓷盘是从何拣来的呢?老何说是他一天拣废品时,从垃圾堆里翻出来的。当时谁也没在意这个盘,老何慧眼识中,读了几年书,老何认得盘底的字,所以这就兴奋地带回来,谁也没告诉。李玉其咽了口唾沫,对老何说:表叔,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个假的。老何闷头吸烟,半晌嘟嚷道:我看不像是假的,我也不图它赚钱,就捐给国家。看看老何脸色不大好,我拉拉李玉其,告辞出来。 一路上,我没太搭理李玉其,他也没说话。快到家时,他才闷闷地问我:你说,这会是真的吗?我没吭声,李玉其又肯定地说:不会不会,这太假了,外行人都看得出来。上楼进了家,小梅正在看连续剧,我跟她说今天和李玉其去了老何家,看了他的瓷盘。小梅无精打采地伸了个懒腰,随便应了声。洗脚时,她坐在床边对我说,她今天也上老何家去了,带了相机和采访本,给瓷盘拍了照,回来就拿给市博物馆的人看。人家一看就是假的,赝品。小梅说到此处时,有些愤愤的,仿佛老何欺骗了她。我知道她对好新闻的热情不亚于对我,此刻她的心情我也能理解,失落嘛,不服嘛。好不容易摊上个略有价值的新闻搞了半天是个假的,能不气愤嘛。我拍拍她的后背,说她心态不好。跑新闻这行,哪能次次线索都是真的,人家还报假消息呢,和人家比起来,你的敬业精神太值得大家学习了。 老何上报 没几日我在小梅她们的报上看到一篇小报导,标题是:拣宝心态不正 老汉以假充真。详细内容说了一个拾荒老者拣到一个瓷盘,便大肆宣扬,拣到文物,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等等。看完后,我大吃一惊,以小梅的为人是不大会写出这样失实的报导来的。播了一通电话,占线,打小梅手机,小梅在外面,声音吵地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便挂机下午再给她打。正挂了电话,门被咚地推开,李玉其拿着报纸跑进来,气喘吁吁地问我看了今天报导没有。我点点头,李玉其啪地将报纸拍在桌上,大声说:这也太离谱了吧,这么有失真实。看看我,李玉其沉了脸:王哥,这是不是嫂子写的。我说,不一定,我正打算打电话问呢。李玉其坐下,想了想,说:我上表叔那儿看看去。便推门走人。 下午小梅给我打了电话,张口就说那篇报导不是她写的,是她们主任让一个实习生写的。她也为此努力争取,说是不实报导,可没用,主任说他另派人去调查过,老何不单单来了报社,连博物馆也去了,人家都说了是假的,他就是不信,还到处说,并联系人要出手卖掉。我听了心下里吃惊,老何他不会吧,不像是这样的人啊,挺老实的。小梅那头也感叹道:是啊,我瞧着也是,可这年头,保不齐,你呀,还是别管了。李玉其那儿,你就把我刚才的话对他说了。挂了电话,我也无心办公,打李玉其的手机,想向他说明。结果信号不通,想来他在老何家,那地方可能是信号不好。想想,就先搁下,没找他。 快下班时,李玉其才回来。我跟他讲了小梅的话,并问他老何情况如何。李玉其摇摇头,叹道:这两天不断有人找老何,除了二道贩子,还有公安局的,查老何是否有前科。老何收好了他的瓷盘,见谁问都不说话。人也蔫蔫的,公安局问了几次也就算了。李玉其叹叹气,我这个表叔…… 再见老何 时间匆匆溜走,办事处里开始评干,小梅单位分房,我忙得不可开焦。李玉其新交了女友,也整日里不见人影。新房到手,小梅让我去买木板和瓷砖,在班上时我抽了个空跑到城郊的建材市场。正在讨价还价热火朝天之际,眼角处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老何,他佝偻着腰,正在拖一叠厚厚的纸箱。穿得还是那件卡其布的上衣,深蓝裤子,解放鞋。我叫了他一声,走上前去。老何明显又老了许多,皱纹深深地堆在一起,灰尘和污垢就隐身其中。老何认了我半天,我递给他一支烟,他才恍然,王同志啊。 我帮老何将压扁的纸箱拖到角落,老何坐下来,深深地吸口烟,问道:李玉其还好吧。我说好着呢,谈对象了。老何就嘿嘿地笑了,被烟呛住,干干地咳了几声。我问老何,你是李玉其父亲家还是母亲家的表叔。老何说:他爸那边的,我是李玉其他爸的表兄弟他老婆家的兄弟。我被他那圈关系给绕糊涂,反正是李玉其的远房亲戚就是了。老何,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上次那个瓷盘……老何看看我,低头闷了会说:那确是真的文物呀,可惜没人识得。老何拉住我的衣袖:王同志,你是文化人,你说,这瓷盘是不是真的。我尴尬地笑笑:这,不都鉴定了嘛,确实不是真的呀。老何垂下手,仍一个劲的说:我就不信,我就不信。留着,总能有人识得的。此时,我觉得已无继续搭话的必要了,找了个托辞,我告别老何。临走,老何还拜托我替他留心着,有无识文物的人。 回家,我对小梅说了这事。小梅感概道:这老何差不离快精神错乱了,怎么就认个死理呢。转脸小梅又问我:李玉其管不管老何的生活。我说:大概不管吧,听说老何在老家有儿女,每月会寄钱给他,好像居委会也有补助什么的。小梅想了想,说:看他的生活这么困难,不像是有人贴补呀。哎?小梅登时来了精神似的:你说,这老何会不会是因为家庭矛盾独自来到城里,收废品生活。他有难言之苦呢,又或者他年轻时受过什么迫害?小梅肯定地说:这老何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明天我给主任说说,这是个值得采访的对像,好题材。 有故事的人,老何的身影在我眼前浮现。看来,老何确是要暴出新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