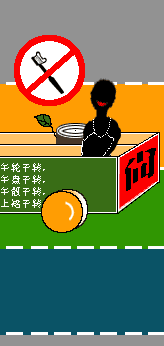|
她挎一篮子衣服迈出家门的时候,抬头望了望天空。天上瓦蓝瓦蓝的,见不到一丝云影。太阳高悬在偏离头顶一点的地方,亮晃晃的像一盆水银。她瞥了一眼便急忙错开了目光。低头的时候,随手往下拉了拉那顶有些发僵的草帽。
现在是正午时分,街上空寂不见一个人影,破裂肮脏的水泥路面流趟着八月炽烈的阳光。没有人会在这盛夏最炎热的时间里走到街上来,连那些平日里东游西逛的狗也都躲进了避荫处,伸长了舌头无精打采地喘息。只有知了单调而响亮的鸣叫,在小镇里连成一片。她沿着街道旁苦楝树一路投下的阴影,独自往河边走。压在右胳膊上的那篮子衣服有些沉,这使她在行走的时候,不得不向左稍稍倾斜一点身子。
老了。她想。
家离河埠并不太远,走到小街的尽头,向右拐穿过小城门就是河埠了。她记起这段路自己已有一年多不走了,但路她是再熟悉不过的。自从嫁到这个小镇上,她几乎每天都在这段路上来来回回,挎一筐衣服或提一篮菜,洗洗刷刷的岁月流逝得无声无息。认真想来,她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是在这条路上给走掉的。只是现在她有些疑惑,都是几十年走过来的老路了,怎么才一年多不走,今天就走得有些吃力和陌生了呢?
她注意到这一路上与过去有了一些不同。
黄桂花的豆腐店还开在老地方,只是店铺前那几根快腐蚀的廊柱被拆除了,现在的店门显得宽敞了许多。豆腐店再往前,原来是一长溜的老木头房子,那是许老佑的家、张全的家、李富顺的糖店和吴皮匠的铺子。现在那里被拆开成了一片平地,乌黑的房梁椽子和破砖碎瓦堆满了一地。
走过刘三家门前的时候,看到那两块光滑的大溪石还凉嗖嗖地躺在屋檐下的阴影里。不过她觉得好象少了一点什么。她往黑黝黝的门洞里望了望,猛然记起刘三的瞎子老爹已经死去很多年了。她想起那些年老瞎子整天端坐在大溪石上,每次听到她从面前经过的脚步声,总枯枯地招呼一句:“和寡妇,洗衣啊?”她心里突然就轻轻笑了起来:这瞎老头子,听说早年骚着哩,染了一身的花柳病,把一双眼睛也弄瞎了,下半辈子就只好让自己的一双卵蛋放在石头上干凉着了。这样想着她的眼睛就再不敢去看那大溪石,腿脚的迈动也不由加快了起来。
走到小街的尽头就看见烟鬼林财旺刚起的那栋小洋楼。这事镇子里传扬了很久,都说烟鬼的两个儿子这些年开车挣了钱,盖新房了。想到林财旺的儿子她就不由皱起眉头。原来多顽皮的两个孩子啊,她想。她蹲在河埠洗衣服,他们就故意从桥上往水里扔石子,常溅她一头一脸的水。记得有一次她跟林财旺说起这事,烟鬼“扑通扑通”埋头抽烟,老半天才冒出一句:“孩子嘛,嘿嘿”。这样没管教的孩子,长大倒造化了,会开车挣大钱了。她抬头看了看眼前崭新的洋楼,胃里突然就翻出一股酸不酸甜不甜的潮水来。
穿过小城门的时候,她觉得右胳膊有些酸胀无力。她把衣服篮子换到左手,右手从竹篮里拿出棒槌。这样,身体就会平衡一些。她在心里轻叹了口气,感觉到自己真是有些老了。
河埠空荡荡的。正午的太阳把沿河一溜平坦坦的石板烤晒得有些发白。下游不远处通往北岸的石桥上见不到人的踪影。靠小镇的南桥墩下小山一样堆积着花花绿绿的垃圾,一个戴草帽的人躬驼着背在上面翻寻着什么。没有风,但她还是隐隐闻到了被太阳烘烤出来的烂塑料和死动物腐沤的臭味。当今的人啊,她心里叹息着,连垃圾都堆到河里去了。
她沿着石阶走下河埠。河水轻轻拍打着河岸,发出轻微而有节奏的水声。正午的阳光在宽阔的河面上碎成一大片闪闪烁烁的光点。河埠两边的堤坝上依旧生长着茂密的水杨梅和鱼胆草。在这个季节,水杨梅正在抽穗,而鱼胆草像公鸡一样翘起一枝枝淡蓝色的花苞。她微微眯缝起双眼,心里感觉到一阵踏实。眼前的景象一如往昔。那一刻,她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时光。
她把衣服篮子放在一块青色石板上。这是她过去最喜欢占用的一块石板,比周边的其它石板都平坦宽阔,石头的质地也细腻光滑。这样的石板是最不容易伤衣物的。她很满意此刻河埠上没有一个人,那块石板斜斜地插入水中,静静地等着自己。这是我的石板哩,她想,然后蹲下了身子。可她马上就又站了起来。石板被太阳晒得热烘烘的,灼人的气息直往胯下冲。她四下里巡视了一遍,猛然想起河埠边原是有一棵大樟树的,那树荫正好可以遮盖住大半个河埠。现在她看到那个生长樟树的地方只剩下一个布满干苔的树墩,大树和它的树荫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有些怔怔的。对一些旧事物的回忆使她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她在那块大青石板上重新蹲下来。感觉到有些吃力,膝盖骨发出一阵轻微的咔咔声。她尽力挪了挪身子,让自己的重心往后沉一些。连骨头都老了,她感慨着,一边把右手伸进了河里。
河水的沁凉一下就从手指间传了上来,迅速流遍全身。太阳热辣辣地烫在背上。她觉得把手伸进水中的感觉真是舒服,这一刻她真想连人都泡进河里去。她记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总是捋起裤腿站在河岸边的浅水里洗刷,与一群同样年纪的姑娘媳妇嘻嘻哈哈的互相甩泼水花,引来桥上经过的男人一串串异样的目光。是从什么时候起就不再下河了呢?她晃了晃脑袋,发现自己记忆中的那段时光一片模糊。
她决定不再去想过去那些事了。她把手从河里扯出来,顺势往脚下的石板泼了两把水。水从干热的石板上漫过,激起一片轻微的声响。
她把第一件衣服从竹篮里提出来的时候,听到身后镇子里传来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她知道今天是镇东头老赵家的女儿出嫁,街坊邻居们都去喝喜酒了。她想象着此刻自己的儿子和媳妇也挤在闹哄哄的宴席上,呼朋邀友地吃喝,心里就有一种小小的得意。就像她从前到吴富顺的糖店买糖时偷偷多抓了一把糖,那种得意不是一把糖的得意,而是因了计谋的成功所诱发出来的得意。她想起中午儿子临出门的时候对她说,妈,吃过饭就歇着。她想:等他们喝得醉熏熏回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想到我正偷偷在河埠上洗衣服哩。
这样想着,她心里突然就有些愤愤起来:哼,有了洗衣机,我就不能再洗一件衣服了?
她一直想不通儿子用板车拉回来的那台哗哗乱响的机器究竟好在哪里。衣服丢进去那么转几圈,也不搓,也不捶,拎出来就往凉杆上挂,这样不干不净的衣服也能往人身上穿。当今的人啊,她轻轻叹息一声,懒得都没法说了。
她把篮子里的衣服一件件往外拿,小心地堆在脚边的石板上。她手里摆弄着这些衣服的时候,心里就有一种十分慰贴的感觉。这些都是儿子小时候穿的衣服,是她从老红木箱里翻出来的。衣服都很旧了,但折叠得很整齐,都是很柔软很结实的棉布和卡其布料,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樟脑的气息。
她记不起自己这一辈子究竟为儿子扯过多少衣服,只知道儿子一年年长高,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腿下来,她从娘家陪嫁来的那个红木箱子也一年年满起来。直到有一天,一个小小巧巧的媳妇进了家门,儿子就不再由她扯衣服了,她的红木箱也就再没有添加过什么了。
河面上吹来一阵微风,带来了一丝惬意。她把手中的那件月白色衬衣迎风抖开,太阳光透过细密的纤维缝隙直逼过来,像一大片明晃晃的银针,衬衫在她的的眼中因此变得透明而虚幻起来。
也许我能记起这是儿子几岁时穿的衣服,她想。
她将衣服轻轻一抖,平平浸入水里,可马上就被水流漂浮了上来。现在她记起来了,这是儿子十三岁那年夏天穿的衬衫。多好的白洋布啊,摸在手上依旧是那样厚实。她记起那年许老佑的媳妇坐月子,自己去帮了一个月的工,挣的钱刚好为儿子扯了这件衬衣。
十三岁,她想,儿子刚上二年级哩。她微微直起腰,用手背撩开一绺垂挂在眼前的灰白头发。她一边把衣服从水中提上来,一边在脑子里极力捕捉儿子十三岁时的模样。
一双稚气的眼睛开始在她眼前眨动起来。儿子是单眼皮,左眼比右眼稍大一些。接着一个酒窝从记忆里跳出,浅浅的挂在左脸上,带一丝羞涩的模样。她记起隔壁的老四嫂常对她说,你儿子将来是个喝酒的料哩。
他确实能喝酒,现在他喝起酒来就跟喝茶一样。她想着,心里就生出一些自豪。想象着儿子此刻在老赵家大碗喝酒的情形,不禁微微笑了起来。
她的笑容映进了河里,被荡漾的河水一圈一圈地放大。她把水淋淋的衬衫放在石板上,眼睛盯着自己的影子出神。现在,她又用嘴轻轻含住了儿子那双粉白晶莹的耳朵。多诱人的一双耳朵啊,她心里说。就像两朵新鲜采下来的白木耳。她想起那些年,儿子被抱在怀里的时候,自己总忍不住去轻咬他这双小巧透明的耳朵。
她将手中的衣服重重地搓揉起来。这会儿她有些气恼,她发现自己怎么也不能将刚才捕捉到的那些碎片拼凑起来,儿子清秀灵巧的五官在她的回忆中时隐时现,像水中那群窜来窜去机敏的小鱼,总难以看得清晰和完整。
她摇了摇头,一股莫名的伤感和这正午的烈日一起哄哄地烧烤着她。她感到脑袋有些发胀,细汗从额头上和身体的其它部位冒了出来。不远处,一片青菜叶子从上游水面上缓缓飘浮而来,她不觉伸出手去,可菜叶又从她面前飘开了。
她开始把石板上所有的衣服一件件往河里浸。每一件衣服从水里提上来的时候,都变得沉甸甸的,发出一阵阵喧哗。这种熟悉的水流声让她渐渐平静了下来。她从湿漉漉的衣服堆里扯出一件铁灰色的外套,将它平平摊在石板上,仔细地打起了肥皂。她知道儿子的衣服哪个部位最容易脏。儿子的脖子很会出汗,他写作业或吃饭的时候总把小臂整个放在桌面上蹭来蹭去。因此,她一般总要在衣服的领子和袖口处多上肥皂。外套是卡其布料的,很厚,堆在石板上很大的一团。过去她是能够很有力地搓洗它的,可现在却感觉到有些吃力了。她深深吸了口气,从竹篮里抽出棒槌,使劲地捶打起来。
这件外套是儿子二十岁生日时买的,她回忆着。那时他已经像个大男人了,嘴唇周围生出了一圈细细的胡须。他多象他那死去的爹啊,她心里说。他们就象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
想起自己死去多年的男人,她就有些伤感起来。
我总算对得起你了,死鬼,她自言自语道。我把你的儿子拉扯大了,我吃了很多的苦,有些事情你不一定会明白。
她心里有些酸酸的,感觉到眼角处有水趟下来,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她用手背擦了擦,继续跟丈夫诉说起来:我为你守了快四十年的寡了,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的儿子也养大了,可儿子养大了又有什么用呢?她愤愤地用棒槌甩打着衣服,嘴里发出了声音:他有了那台鬼机器就不要娘啦!
她感觉到眼睛里又有水不断地涌出来,这回她知道自己是在掉泪了。她不再去擦拭,只是让头低低地垂下去。她看见泪水滴落在手中的衣服上,听不到一点声响。
儿子的衣服从来都是我洗的,她想。既使后来他娶了媳妇,生了女儿,他的衣服也一直是我洗的,从第一片尿布开始洗到今天,快四十年了,我可从来没抱怨过什么。
可现在他嫌弃我了,她心里说。他宁愿花一千多块钱买一台机器。
她想起这一年多来,心里一直空落落的。她总弄不懂自己干了一辈子的活,怎么突然就让一台机器给抢走了。她想,如果不洗衣服,那活在这世上还能干什么呢?
她很早就想和儿子说说这件事了,可儿子总是很不在意的样子,总不肯坐下来认真听听她的想法。现在她想起来了,她是跟儿子说过一次的。那天她装着很随意的样子,把儿子换下来的衣服抓进篮子。临出门的时候儿子却拦住了她,眼睛里流露出很不解的神情。她对他说,机器洗不干净的,还是我拿到河里去洗吧。可儿子却笑着把篮子里的衣服倒进了洗衣机。
记得儿子那天对她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就别忙乎了,歇着吧。
儿子大了,她叹息道,现在他说了算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跟他提洗衣服的事了。她心里说。
她把手中的蓝色外套扯开,放进河里漂洗。面前清澈的河水一下变得浑浊起来,在水底游曳的一群小鱼也突然不见了。她想起儿子小时是很听话的,她在家门口做针线的时候,就把他关在屋子里读书。林财旺的两个儿子总想诱他出去。他们爬在后窗外的梨树上学鹧鸪叫,学画眉叫。可是他从来不出去。他听她的。
也许儿子说的对,她想。现在年代变了,什么都变了,连儿子也变了。
她重重地叹了口气,把水中的衣服提上来,用劲将水拧干,丢进身旁的篮子里。现在她觉得浑身燥热起来,汗水在全身上下爬来爬去,湿透了的衣服紧紧贴在脊背上。她抬头看了看天,天空依旧是那么单调的蓝,太阳好象又偏了一点,几朵白色的云散散地停在远处的山顶上。一张竹排在桥洞下面的阴影里,正一点一点向下游移动。打渔人的脸被竹笠遮着,她看不清那人的脸。
垃圾堆上那个躬驼的人影也不知什么时候消失了。
真热。她想。往年的夏天可从没这样热过,现在连天气都变了。
她把又一件衣服浸入水里的时候,看见水面上飘浮过来一片黄灿灿的谷壳。 她觉得有些诧异。她想起镇里的水碓早几年前就被拆掉了,现在镇里人都挑着箩筐去桥北岸的碾米厂了。眼前这些谷壳是从哪里漂来的呢?她抬头往上游望去,不远处的水碓悄无声息,黑乎乎的水车斜靠着破烂不堪的碓房。在明亮的太阳光下,生长在水车上和渠道边的青草依稀可辩。
她伸出手从水中打捞起一把轻飘飘的谷壳,心里面突然就想起了守碓人二爷。
老光棍二爷是个逃荒来的外乡人。她还没有嫁到这镇上的时候他就守在碓房里了。自己的男人死得早,她想起那些年二爷总是帮她将碾好的米挑回家中,帮她把装谷糠的麻袋扎紧了放在墙角。闹灾荒的那几年,他把别人椿米时遗漏下的碎米一点点收拢来,让她用衣角包着偷偷带回家。她是知道二爷那点意思的。她也知道那几年街坊邻里看她和二爷的时候,眼神都怪怪的。只是不久之后的一个夜晚,二爷掉进了碓房外的水渠,让水车给碾成了肉饼。她和他之间最终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这个时候她想,如果当初二爷真的把那句话说出来,自己会不会答应呢?
她突然就觉得自己有些不要脸。她在心里恨恨地骂了自己一句:真是老不死了,还想这种混事。她想,如果当初真的做了什么,让儿子怎么做人呢?
这样想着,她在心里就怨怨的白了儿子一眼:我苦了一辈子可都是为了你,你这没良心的。
她把手中的衣服在石板上用力搓揉了两下,然后停下来。这会儿她感到双腿有些麻木了,头也有点晕眩。眼前总有一个黑点在晃动,汗水渍进眼里,火辣辣的疼。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流泪了。
她小心地挪动一下身体,把重心放到右腿上,让左腿放松下来。然后把手中的衣服拧干,放进篮子里。她想,我不会跟儿子说这些的,我什么也不会跟他说的。
其实跟他说了又有什么用呢?她心里轻轻叹息道。他不会有空听我说这些的,他会认为我老糊涂了,该入土了。
石板上堆着的衣服已经不多了。她又一次抬头看了看天,天上还是没有一片云,太阳开始移到石桥那边去了,桥的阴影被拉长过来,斜斜地横在水面上。她想,等桥的影子爬上北岸那棵最大的木槿花树上的时候,我就会洗好了。她突然有些担心,她不知道自己提着一大篮子洗好的衣服进门的时候,儿子会怎么说她。
我不管他,她想。我不会在乎他说什么。
也许他还没睡醒吧,她又想。
现在她觉得右腿太累了,她只好再一次移动身体,将重心放到左腿上,同时从衣服堆中拿出一件来,把它漂在水里。这会儿她觉得头一阵阵发晕,太阳穴一抽一抽的疼痛。我这是怎么了?她在心里骂自己。真是不中用了,洗这么一点衣服也不行了。
她记起过去每次来河埠洗衣服,都提着满满的一大篮子。那时候她可从不觉得自己会有什么不行。也才一年多,她想。我就老成这样了。
她深喘了一口气,然后从河里捧起一掬水,嘬起嘴喝了一口,但马上就又吐了出来。她发觉这水有一股怪味。她转过头,看了看上游不远处几根滚滚冒烟的高大烟囱。这世道,她骂道,真是越来越不象话了。
只可惜了这条河。她想。
她重新捧起一掬水抹在脸上。水的凉意一下让她清醒了许多,她发现自己的脚不知不觉都快踩进河里去了。她小心毅毅地往后挪动了一下身子。她记起有一年冬天,也就在这块石板上,因为上面结了冰,她一踩上去就滑进了河里。当时那个冷呵,她觉得连骨头里面都结起了冰渣。她想象着自己当时落汤鸡一样从水中爬上来,全身乱颤的怪模样,不竟微微笑了起来。
那时年轻,她想。如果是现在,这把老骨头就休了。
她用劲地搓洗着那件深蓝色的衣服,亮晶晶的肥皂泡和水泡从她枯瘦的手中不断涌出,沿着倾斜的石板一串串滑入河里。她感觉到时间好像停止了,只有太阳的热度越来越高,连吸进鼻孔里的空气都是辣辣的,让她觉得有些喘不上气来。
搓揉手中这件衣服有些吃力,她觉得自己的双手快抓不住它了。可是她不想用棒槌。她在心里自言自语:这是儿子念中学时穿的学生装哩。
她记起那些年自己手头紧,儿子念三年初中都穿这件学生装。每次洗这件衣服她都不肯用刷子和棒槌,凉晒的时候也要将它翻过来,怕被太阳晒旧了。那时她看到儿子穿着这件外套匆匆忙忙去上学,心里就有些酸酸的。
她把衣服漂进水里,然后提上来细细端详。她有些感慨。都穿了三年了,还是好好的。
她觉得头又开始眩晕起来,河水闪着白光,在眼前晃来晃去。
你真是不中用了,老东西。她心里默默对自己说着,一边放下衣服,用手撑住有些晃动的身子。这会儿,她看见河面上又漂来一片葱绿的青菜叶子。
她把手伸出去,可菜叶又飘开了。她有些气恼地拍打了一下河水,看见水中一群小鱼被惊散了。
她记起儿子小时是很喜欢小鱼的。那些年,儿子有时跟她去河埠洗衣服,总静静蹲在那棵大樟树下,手中捧着一个玻璃瓶,等着她为他捉小鱼。她每次往玻璃瓶里放进一条小鱼,儿子都会欢天喜地,哇哇乱叫。
那时他多听话啊,她说。
她突然感觉到面前的河水开始旋转起来,眼前一阵发黑。她急忙闭上眼睛。就在这一刻,儿子小时候完整的形象一下在她脑海中清晰起来。白嫩的脸蛋,眨动的眼睛,酒窝,耳朵,羞涩的笑容……。
她睁开双眼时候,儿子却又不见了。
离岸不远的水里,一件深蓝色的衣服正缓缓地飘浮。
儿子。她心里急叫一声,立即伸开双手向河里扑去。
她觉得手中抓住了什么。
儿子。她想。我抓住他了。
傍晚时分,一个中年男子神情不安地在河埠上张望。他看到河埠空荡荡的,沿河一溜平坦坦的石板在太阳的余辉下有些发红。一只竹篮装着大半篮洗好的衣服,孤单地搁在一块青石板上,一根棒槌斜斜横在旁边。
他扭头往下游望去,看到太阳已经快下山了,血一样红的晚霞铺满淡蓝的天空。许多人在不远处的石桥上走动。一张竹排悄无声息地隐在桥洞下的阴影里。一个灰色的人影在桥墩旁的垃圾堆上晃动。
不久,天就完全黑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