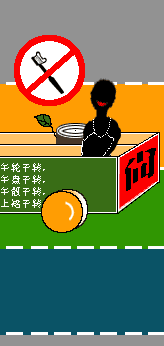
|
路轨
扫红
|
| 从幼儿园门口出来的时候,我的情绪还没有平静下来。小东西的不合作令我想毁掉两天前与他订的合约:如果星期一、星期二都好乖乖,星期三我们就去买下他很早就相中的一套高架组合路轨。商场在98C的终点站,我们住在终点站之前的两站。如果放学时他仍然讲不出老师究竟教了些什么,我们就会在终点站之前的两站下车,不去终点站那家商场,不买玩具。他一定会哭,会赖着不肯下车,然后我把他丢在98C的车门口,独自下车,扔他在车上哭到昏天黑地……我一路就这么想着一边往地铁站走去。这个下午我要去旺角的潮流特区替一个亲戚看店。她有个女儿与我的小家伙差不多大,她母亲今天有些事走不开,请我替她几个小时。
我拿出八达通在地铁闸口上“嘀”了一声之后,就进了地铁站。迎面两个工人在维修那台政府设置的生活易电脑,我想起上个星期曾在这台电脑上跟政府预约了换领身份证,又想起昨夜梦见自己所有的证件和钱包全部不见了,然后想到给几个朋友的书,上午刚刚寄出去。它们在经过内地海关时会不会遭到海关人员的拆检?以前我在内地收到国外朋友寄来的书时,所有的包装都被拆开了,然后贴上一个海关检查的黄色小标贴。我们打赌,输了的几个人拿出礼物来,然后大家相赠。但我知道除了我他们都没有做,他们说说而已,做的只是我。再然后我想到口碑,我的口碑一向很好,这会给他们小小的感动。小小的感动,我忽然看到一张非常变形的画,奇幻旖旎,眨着长长的睫毛冶荡的孩子般看我。我就冷笑起来,觉得感动是一种多么不值得的情感,它远远没有“震憾”来的有力。可是,力量,这东西从哪里来?我走下楼梯来到月台,感动与震憾,它们两个摇摇晃晃的在我眼前比较。我从手袋里拿出笔想记下些什么,笔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偏偏今天忘了带上笔记本。于是翻出夹在童话书里的一张儿童杂志订阅单,它的后面是纯白的,象雪、婴儿的屁股、一只鸟落下来的羽毛。童话书是每天都要在身上带一本的,我们搭漫长的巴士的时候,就给小家伙讲故事,但是现在我发现小家伙中了童话的毒:他除了我讲的故事,其他的什么也记不住,每天从幼儿园回来,唯一能够记住的就是当天的茶点吃了什么颜色的糖。我刚才发脾气也是因为这个:他不告诉我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我们两手空空的去到学校,在老师的询问之后才知道他的隐瞒。不,他不是隐瞒,他是空白,他不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知道家庭学校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知道应该认知什么和做什么,唯一知道妈妈会讲故事。我意识到这一点时非常生气,气他为什么不能跟其他孩子一样,自然的接受一些自然的事;也气自己用了这么多心思浇铸出这么一个脱离现实的孩子。我拿出笔垫着这本童话书在纸上写:“感动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件事,远远没有震憾来的强烈,装载它们的容器相互……” 这时候我脚下一空,从月台上掉下去了,摔倒在两条路轨中间。我的左手肘部和膝盖,还有臀部,摔得生疼生疼,那本童话书就在旁边,那张记录了我思想的订阅单却飘到两米多远了。地铁站里一向都有着很大的气流,有时候我甚至刻意站那么近,让气流从脸上刮过去,头发在脸上和脑袋周围肆意飞舞,我象个疯子,恶意的笑笑。 当我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时,我忽然快乐起来──我正趴在两条路轨中间──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又刺激的事情!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和几个同学一起不上课,大摇大摆的从学校走出来,招一辆“麻木”,我们把当地那种三轮车叫“麻木”,因为它可以把你颠簸到全身麻木。我们招了一辆,或者两辆麻木,去到火车站,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火车站,在京广线上,由南到北的火车开到这里必须停下来加油,然后再向北跑向河南河北北京。如果不加油,它就跑不过我们北方那一片连绵的崇山峻岭,那边的山很大,大到我爱上它,想把它当一个男人,偎在他怀里。但那天我们没有向北走,我们顺着铁路一路向南行,我们几个男孩女孩,非常亲密的,拉着手唱着歌,在京广线的铁路上愉悦的走着。有时走在中间的枕木上,有时好玩的牵了另一人的手踩在窄窄的路轨上,路轨被南来北往的列车磨得发亮,闪着阳光。我们议论那些跟着路轨有多远走多远的电线杆子,那些电线,我们说那些电线契而不舍,它们最多有几只麻雀来点缀一下,但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感动的精神,我们很羡慕一些什么,但都说不出来。我们还摘了路边的野花戴在头上,女孩子都很喜欢这个的。那天我们三个女孩恰好是全班最漂亮的三个,几个男孩也是很出色的,他们的画都很好,其中一个的水彩画尤其漂亮。路边有过人高的草状植物,我们都叫不出名字,有人说是“篱蒿”,有人说是“篙笆”,还有人干脆说是“芦苇”。路边还有一些房子,里面住着人,他们的衣服就摊在那些低矮的灌木上晒着,很“跳灿”的颜色,一个男生就批评,说这些衣服的颜色很“夹生”,穿出来很俗。那个下午的阳光象秋天,渲染着我们,我们就这么相亲相爱的走到夜里,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一直走到了岳阳城,我们站在岳阳楼上,看好大的湖啊…… 月台上忽然忙乱起来,有人尖叫,有人嚷着:“快点按制!紧急制动!”有人往后退,又有人匆匆跑过来。“喂!快点上来!”一个人向我伸出手,我茫然的看着他,这个牛仔裤的中年男人。我不喜欢穿牛仔裤,它筘得我紧紧的不舒服,我喜欢穿女人味浓浓的裙子,不过好在今天我没有穿裙子,我穿了一套新买的秋装,啡色的斜纹布长裤和啡色的淑女布鞋。那男人微微有些发福,着急的向我伸出手,一边向地铁将要来到的方向扫了一眼。我不大想上来,也不怎么害怕,不,是完全没有害怕,反而沉浸在一种很透明的快乐里面,这快乐甚至有些凉凉的,沁人脾骨。我顺着那人的脸看到他蓝色的短袖再看到他那只很干净的手,向我伸着,似乎可以感觉到那只手上的热度。被一个人的手握住是一种多么温暖的感觉啊,可是我拒绝。我的表情一定很奇幻,我清楚的感觉到身体的扭曲和痛苦,然后动了一动,由趴在路轨中间变成坐在其中一条路轨上面,姿势很不雅。这条路轨也是发亮的,但它反射的是灯光,不是夕阳,它漆黑的,沾满了油腻腻的烟尘。芦苇花飘散了,纷纷向河里堕去,它们穿过一个又一个隧道,坚定不移。这时候我低头检查自己,最痛的是左腿,跌下来时它正好磕在钢筋的路轨上,它一定青了,我的左手肘部和右手都受伤了,往外渗一些血,殷红殷红的,这颜色那个男生该不会说它“夹生”了吧?我捡起童话书,随手把手袋拉好,那张记录思想的订阅单躺在后面,我扭头准备去捡,一个女人嚷起来:“莫捡啦!快点上来呀──”几个肥胖的女人向我招手。她们全部穿着花短袖上衣,烫着头发。 我刚站起来准备去捡那张订阅单,两个穿白衣服的男人跳下来把我一拉,然后很有力的把我往月台上推:“快点先上去吧!捡命要紧啊!”我挣扎,我想他们不明白我要捡回那张纸,是啊,念头在每个人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行动出来时别人怎么能够知道呢?想法和感觉是最隐晦的东西,它们随时千变万化,从不知名的地方来,穿过你然后若无其事的走了,不走的就留下来拼命的挠你的耳朵。我原谅他们的不理解,推开他们向订阅单走去,可是他们的力气远远大过我,说:“有什么上去好好说吧。”另一个也说:“是啊是啊,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呢?”他们显得很紧张,大概怕延误班车,明天的报纸上又要炮轰地铁公司了。我笑了一下,说:“不是,”然后我还没说完就糊里糊涂的被几个白衣人合作弄上月台了。 月台上围了一些人,他们有男有女,进行着深切友好的交谈,有人把我按在一张椅子上,一个身上有着绿“+”字标志的人给我洗手臂上的伤口,这时我才发现这些白衣服的人都是地铁公司的员工。他们统一穿着藏青色的长裤,白色短袖制服,肩头上佩着蓝色的肩章。 “你没什么事吧小姐?有什么可以慢慢想,记得要留些余地给自己啊。” 我想起来,这是刚才拉我的那个男人。是他阻止我去捡回思想的订阅单,是他把我从一种透明的快乐里面拉回来。我憎恶这个男人,虎视耽耽的看着他,用舌尖添添口腔里面右边的尖牙,两朵云霞从他眼睛里飘过。我的背部正中间开始向外长草,然后迅速的往上抽,越长越高。 “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麻烦?”我楞了一下,想起刚才进地铁站之前的气恼,“我的孩子……”我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呢?说他没有记忆能力,还是说他没有认知能力?这个东西很难表达,他的问题是外在看不出来的,可是存在就是存在,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你的孩子?”他疑惑的看着我。 “是。”我点点头,肯定的看着他,我拍拍手上的童话书,“他,完全生活在童话书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可能理解也可能误会了,说:“哦,你让你家里人来接你好吗?” “家里人?” 替我包扎的人抬起头来对我说:“你的手现在没事了,你身体其它部位还有没有不舒服的?需不需要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 去医院检查?我这才觉得事件荒唐起来,发生了什么?这么多人围观,他们一定是把我当成什么了。我想起来,我不去医院,我要捡回那张记录着思想的订阅单,那上面写着什么?感动和震憾,我需要的是哪一种?我刷的站起来,把他们吓了一跳。马上又把我按住:“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不是啊,我要去捡那张订阅单。” “订阅单?什么订阅单?” “那张,有思想的订阅单,唉!你们不明白的了!” 我推开他们走到站台边,他们紧紧的跟过来。这时地铁的班次已经恢复,月台上的气流明显增强了,有轰隆隆的噪音由远及近,地铁进站了。我看到那张有思想的订阅单开始翻飞起来,它那么轻薄,从左至右掠过我的眼前,继续向右翻飞过去。我伸出手,刚才那白衣男人忽然上前抱着我向后退:“你干什么?!不要想不开……”他把我的两手连整个上身一起筘住,以至我无法推开他,我扭过头去看他,他的表情令我觉得很可恶,刚才也是他,把我从一种久违的快乐里面硬拉回来,现在又拉住我干什么?我全身的血液扩张起来,气流更强了,我看到左边尽头列车的顶上一道强光。安娜卡列琳娜,她跳着芭蕾舞在列车的强光和轰鸣中旋转,一段独舞后,慢慢的伏下身子。我忽然乐不可支起来,觉得这游戏越来越好玩了,象真的一样。他们不停的在暗示我一些什么,这时所有的暗示成了明示,我的快乐又来了。越来越强的气流在混乱中催化我,把快乐推向高潮。我楼高百尺,旁若无人,我背后那些茁壮的蒿草摇曳生姿,我兴奋成一望风雨之前深绿的草原,辽阔无边,牧野云低,姑娘们含笑,马儿静静的聆听云的脚步,所有的野花在我的头上,脚上,乳房和丰腴的大腿上,漫天遍野的开放。 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了,我思想的订阅单在气流中翻飞几次后紧紧的贴着路轨里面的墙壁,不动了。我有种去拯救它的责任,它可怜兮兮的被气流颠来倒去。对,我最后写下的是容器两个字,装载它们的容器这时一定碎了,感动和震憾被狠狠的抛出来,向四面八方倾泻──它们需要拯救。我奋不顾身的跳下去,白衣人死死的抱住我,向他的同伴大声嚷着。我扭过头看他最后一眼,露出尖尖的牙齿向他咬去。 “然后火车就从妈妈身上又碾了一次。”
|